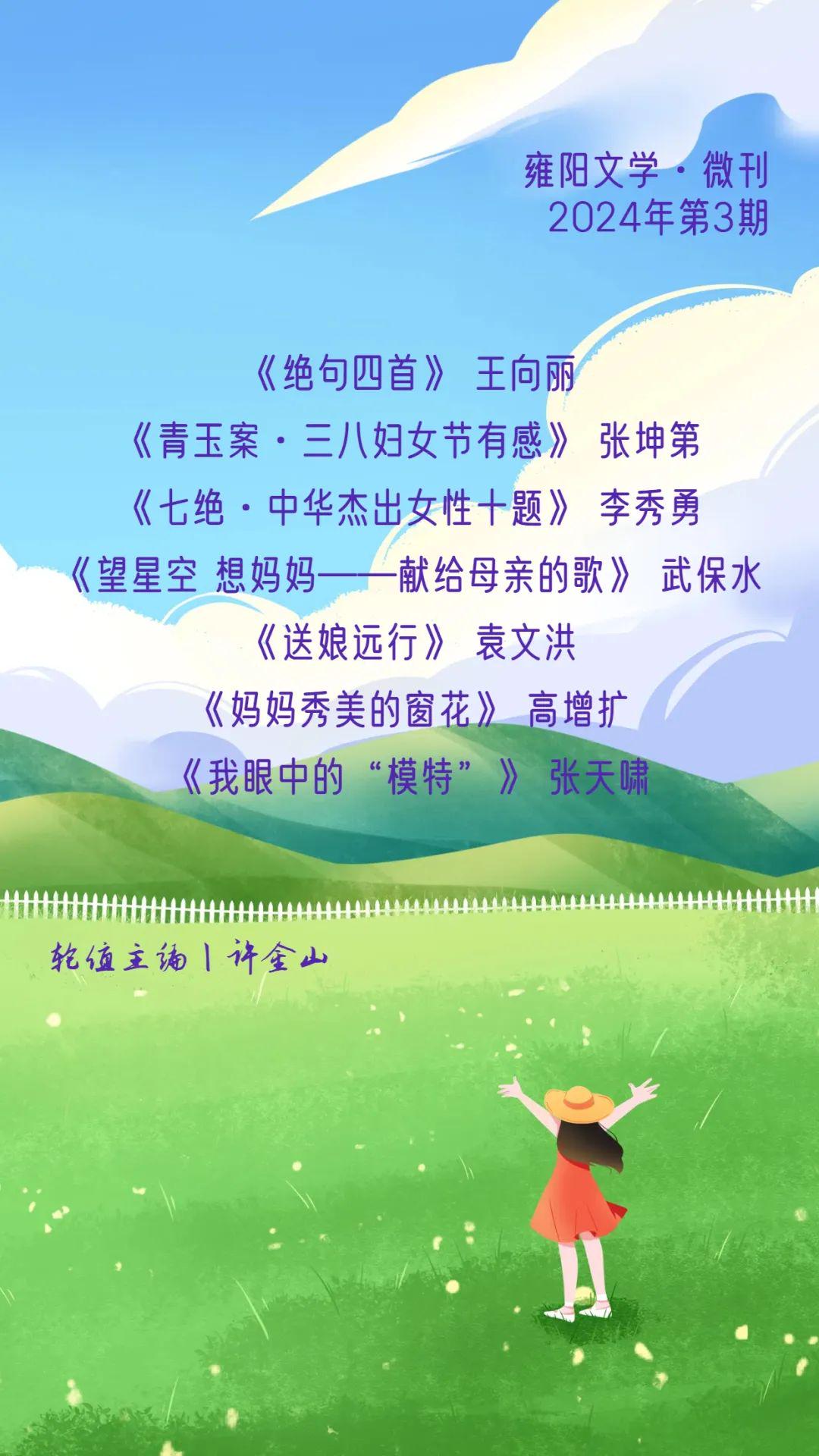
风和水涨春日丽,草长莺飞燕子回。三月,温暖、舒适、宽厚、温和,她是春天,但她也属于女性。她唤起我们蓄积了一个寒冬的那股涌动的心潮,去发现她,赞颂她。当“以文化人”的声音传来,另一个春天也会悄然来临,“何不藏英待时发”?因为我们已经感觉到,人间“自有阳春三月天”。
绝句四首丨王向丽
桃花二题(一)
幽香一缕到谁家,两两三三缀碧纱。
只许风流高洁客,氤氲和墨染春华。
桃花二题(二)
清风二月瘦桃枝,几许仙花几许痴。
陌上曾经沧海色,斜阳暮里染成诗。
绝句·迎春花开
娇花朵朵色均匀,晓雾迷离浣洗新。
几款鹅黄寻梦曲,参差冷墨俏迎春。
绝句·玉兰花开
经风历雨绽坤乾,谁许春光云外看。
抛得万千烟火色,涂丹琢玉自如仙。

王向丽,女,生于天津,研究生学历,武清区直机关工作,笔名君不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天津武清诗词协会会员、天津武清作家协会会员。
青玉案·三八妇女节有感(贺铸格·十八部入声)丨张坤第
春风三八花先发。
满眼景、欢心悦。
醉慕坡亭梅若雪。
楼堂厅院,遒枝劲茁。
洽雅娉高洁。
任谁彩绘霓云缬。
太白难题半天阙。
阅百代儒人史杰。
择邻教子,木兰围猎。
江竹筠情结。

张坤第,笔名楚石。曾服役于空军航空兵某部,现为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散文研究会会员、天津市诗词学会会员、武清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空军报》《天津日报》《天津每日新报》《天津作家网》《天津诗词曲社微刊》《准风诗刊》《天津诗词》《书香诗苑》《雍阳文学微刊》《武清资讯》《家庭保健》《星期天》《运河》等全国多家纸质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
七绝·中华杰出女性十题丨李秀勇
一.孟母
三迁故事永流传,仉氏高风铸圣贤。
但使当初无此氏,儒家文化可曾延?
二.王昭君
当年出塞响驼铃,一片冰心动汉廷。
纵是千般非称意,汉匈和好万家宁。
三.蔡文姬
胡笳千载动肝肠,谁解文姬异域伤?
堪笑曹公倾汉祚,三分何处不凄惶。
四.花木兰
替父从军十二年,遂令忠孝两成全。
男儿谁个堪相比?枉在英雄簿下眠。
五.谢道韫
咏絮才人出谢家,千秋万代傲中华。
须眉低首因惭怍,内史夫人谁不夸?
六.李清照(通韵)
生作人杰死作雄,易安豪气贯长空。
须眉不解红颜叹,沉醉余杭迷雾中。
七.秋瑾
龙泉鸣壁壮心怀,敢为乾坤听令差。
血染江山何所恨?已将火种递同侪。
八.冰心
繁星春水记心间,小小桔灯迷少年。
片片纯真飞海外,晶莹温婉爱无边。
九.杨绛
一腔正气净红尘,不做追名逐利人。
百载生平称典范,书香袅袅慧斯民。
十.叶嘉莹
迦陵行迹遍寰中,惠及东西谁不崇?
文化传承真大计,春风催雨化长虹。

李秀勇,笔名梦之林。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武清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研究会员。曾在《天津日报》《中国诗词》《诗词报》《中华风》等多家纸媒和网络平台发表诗歌和散文。
望星空 想妈妈——献给母亲的歌丨武保水
亲爱的战友
你可曾记得
当年的绿皮火车
把我们一路拉到天涯海角
从此告别母亲远离家乡
投入到炽热的军旅生活
每当我在海边站岗巡逻,
仿佛望见妈妈的泪眼,
端详着儿子椰树下的留影,
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快乐;
每当我在战舰里头枕着波涛,
无不梦见你呀,
还在灯下拆洗着我的棉裤棉袄,
那双曾为八路军做过军鞋皴裂的手
浸泡在冰水中,
一刻不停地揉搓,揉搓……
每当我目送战鹰滑入跑道冲向蓝天,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诉说:
雄鹰啊,
你能不能飞向北方飞到家乡?
带给妈妈一个问候,
孩儿时刻记着临行前您的嘱托。
妈妈呀妈妈,
你用全部的心血将儿养育,
你用甘甜的乳汁解儿饥渴,
你用仁慈的母爱教儿做人,
你用坚强的意志领儿爬坡。
儿记得
那年的风雪特别地大
十里之外的孩儿放学难回家
您竟倚着门框静静等候到日落
还记得
儿在部队连续两个春节未回家
第三个春节答应您一定回来过
高兴得母亲颠着小脚
忙前跑后备年货
未曾想因战事又耽搁
您精心蒸制的年糕
出了正月还在屋后的阴凉处
给儿留着……
半个多世纪过去
岁月如歌
我站在妈妈曾经伫立的村头
模糊的泪眼仰望灿烂的星空
亲爱的妈妈呀,
您就在那啊——
天河里最亮的星星一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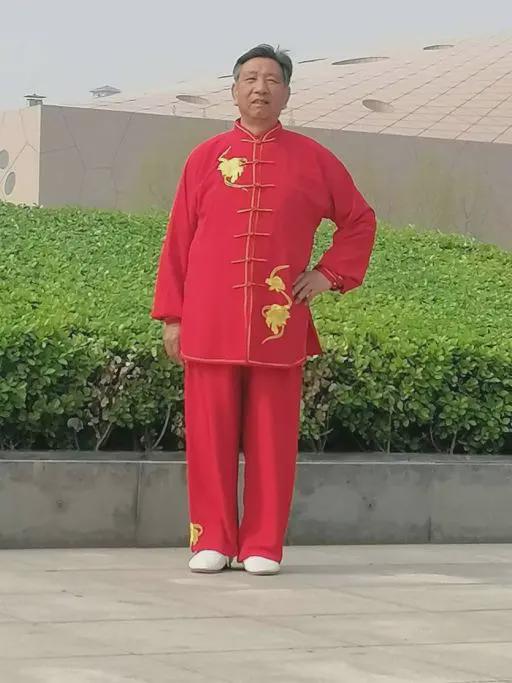
武保水,男,1952.10生人,天津市武清人。1970.12参军,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服役。1997.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毕业。业余爱好文学创作。2007年以来在《天津中老年时报》《廊坊日报》《武清资讯》《运河》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百余篇。现为武清作协会员、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
送娘远行丨袁文洪
娘要走,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儿不舍,含着泪,看娘。
娘褶皱的脸像道道小溪,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娘两眼浑浊,看着儿,嘴微微蠕动,想说什么已经说不出来了,眼里盈满泪水。
儿的眼泪滑落下来,轻轻地拭去娘眼角的泪水,抚摸着娘花白又有些零乱的头发。
娘笑了,神情里透着骄傲。
儿哭了,依偎在娘的怀抱,泪默默地流。
终于,娘走了,在一个飘雪的冬天。
儿送娘,哭嚎。
娘踏上了一条通往西天的林荫路。林荫路尽头,霞光绚烂,变幻神奇,仿佛海市蜃楼。娘佝偻的身子像个问号,一步一趋,渐行渐远。攸地,仅剩了一个点儿,融进霞里。
娘不见了,儿哭嚎。
雪,越下越大,弥漫了整个天空。
儿成了雪人,不,雕塑,凝视着霞。
墓地东侧是一片桃园。每到春天,桃花盛开,雀儿“叽叽喳喳”枝间跳跃,蜂儿“嗡嗡嘤嘤”地闹着,果农们在忙碌。
西侧是一条小河,自北向南弯弯曲曲,不知从哪里来又流向哪里去。许是连了大运河的水脉,两岸的桃树、水草、庄稼被滋润得生机盎然。
清明或年节,儿着一身素衣,奉一束鲜花,掬一坯黄土,在娘的墓前祭拜。
娘一生爱儿爱花爱水。这,也算了了娘的心愿。
儿想娘,苦苦寻觅,可再也见不到娘了。儿问天,娘,你在哪里?天不言;儿问地,娘,你在哪里呀?地不语;儿问高山,山谷回音,是娘的悲泣;问河流,河流东归,娘已逝去……
儿一次次回忆娘。娘在田间,在烛光里,在灶旁,在打麦场,在小河畔,在磨房,在土炕上,在篱笆院儿,在老井边……
终于,儿见到了娘:娘在梦中,在霞里,在小河边那片桃花盛开的地方,在飘雪的日子里,在逢年过节和家人团圆的时候,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娘没有走远,始终在儿的心中。
娘因善良而美丽,因无私而伟大。娘大半辈子都为儿女活着。
娘一生以子为荣,从一粒米、一根线、一句话开始教育,希望儿长大成人。报答娘,唯有像娘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生死两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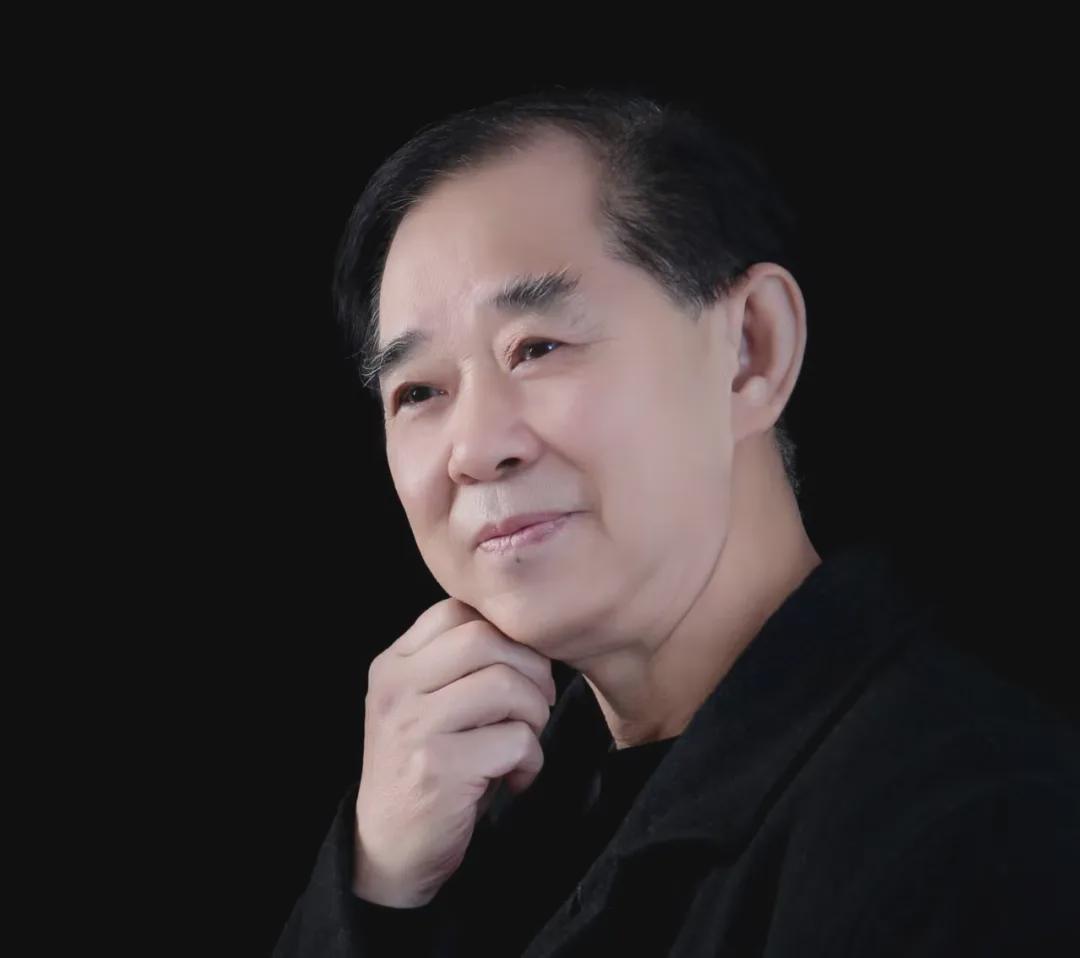
袁文洪,笔名远岸。中学教师,公务员,喜好文字,多篇作品散见省市报刊和中国作家网、天津北方网等网媒;《赢家》《大海的声音》《那一片麦田》等获市级征文奖,入选《现代文阅读》《作文通讯》并作为中学生阅读试题和毕业检测试卷。
妈妈秀美的窗花丨高增扩
每逢节日喜庆的日子,总会唤醒我对小时候妈妈剪窗花的记忆。
妈妈出生在旧社会,家境贫寒,从未进过学堂读书。但妈妈心灵手巧,喜爱学习临摹民间的剪纸技艺,剪得一手秀美窗花。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艰苦,但操办婚事依然红火热闹:新娘穿着红嫁衣,头顶红盖头,洞房内外红喜耀眼。红门帘,红花被,红瓷脸盆,红瓷痰盂,红铁皮暖瓶……当然更少不了大红的剪纸窗花。自从街坊邻里定了大喜日子,妈妈手头儿就忙碌起来。吉祥富贵的“龙凤呈祥”是辅在脸盆里的;大小双喜是贴在大门上、正堂墙上和洞房里的;“喜鹊登枝”、“花开富贵”、“百年好合”是贴在窗户上的……妈妈剪的喜字和窗花,瞬间映红了土坯院子,给萧条的村庄平添了喜气和温暖。
进了寒冬腊月,喝过软糯香甜的腊八粥,吃过小年廿三祭灶的糖瓜,妈妈格外忙起来。白天洗涮蒸煮,晚上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做新衣、剪窗花。在小炕桌上,妈妈先用铅笔在红纸上勾勒出花样子,再抄剪子剪纸。随着手腕的翻转,纸屑“沙沙”滑落,一幅精美的“花篮”脱颖而出:婷婷的茎,细细的叶,匀称的瓣儿,鲜活的芯儿;一帧“金鸡报晓”,金色的雄鸡,引吭高歌,迎来满天朝霞……还有“招财进宝”、“迎春纳福”“、聚宝盆”、“肥猪拱门”等多彩的窗花,与木门上大红的春联、福字相映衬,非常喜庆祥和,渲染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妈妈还按十二生肖,剪出乖巧可人的小虎儿、小兔儿、小猪儿、小狗儿,深得我们喜爱;妈妈羊年剪“三羊开泰”,马年剪“骏马奔腾”,虎年剪“虎虎生威”,龙年剪“金龙送福”,表达了祈盼新春祥瑞、生活平安幸福的心愿。有一年,妈妈剪了个民国时期的“拉洋车”。洋车上坐着个头戴礼帽,口叼烟斗,翘着二郎腿的大鼻子外国佬,我们十分新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外国人”。那外国佬盛气凌人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妈妈还把剪纸技艺拓展到做绣花鞋上。给小妹用红黄丝线绣的小猫鞋、小虎鞋,那猫,那虎,憨态可掬,栩栩如生。小妹穿着绣花鞋,炫耀着走在村街上,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村里的大娘、婶子们纷纷上门求索鞋样子,妈妈笑呵呵的有求必应。于是,荒芜的土街上,靓丽的绣花鞋多起来了,像一朵朵绚丽的迎春花在街头巷尾绽放。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如今,聪慧慈祥的妈妈已过世多年,妈妈煤油灯下剪窗花的倩影渐行渐远,在我心中幻化成一帧泛黄却依然秀美的窗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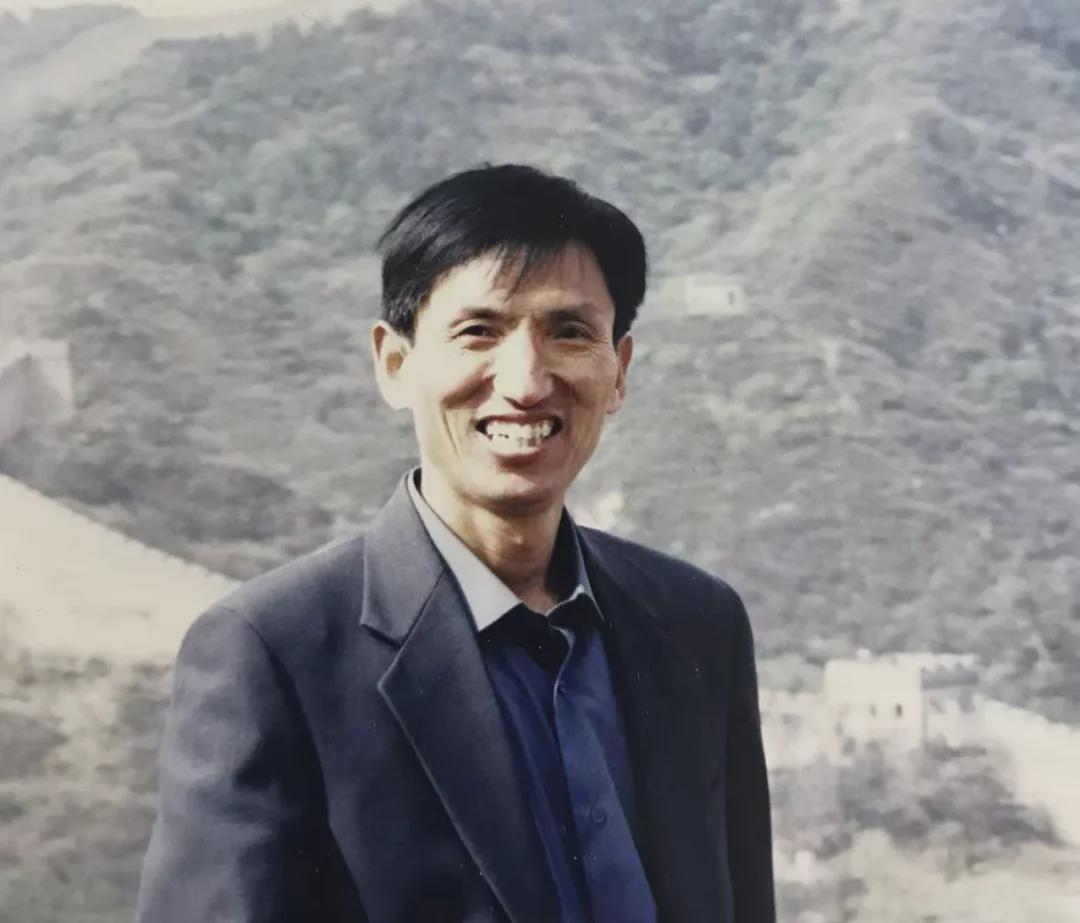
高增扩,笔名晓申。1956年出生,原籍武清。中共党员,退休干部。天津市散文研究会会员,武清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天津工人报》《天津日报》《武清资讯》《运河》《齐鲁晚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学作品。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届第二届“武清你好”征文优秀奖。
我眼中的“模特”丨张天啸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新鲜事物在国内兴起,“模特”一词在那个时候流行开来,在人群中传来传去。随着更多的新型服饰的产出,人们开始注重打扮自己,他们穿上衬衫和喇叭裤,走在街上风度翩翩,在听到别人叫自己一声“模特”后高兴不已。我母亲也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二农机械厂第一位“模特”。
我眼中的模特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我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那些发黄的照片放在了一个有些破旧的相册里,很厚重,像是字典一样。我打开它时,有些照片从相册里流了出来,我急忙用手臂夹住了它们,不想让它们掉在地上。那些照片多半是我母亲的,她梳着高马尾辫,戴着一副太阳镜,穿着深色的衬衫和棕色的马甲,一条笔挺的西裤衬托了她修长的身材,胸前系着一根橘红色的领带,脚上的那双鞋说不好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又似乎是蓝色的。她站在一架巨大的机器前,手搭在那机器的边缘上,向远处看去,模特范儿十足。相册里还有一些她抱着我的照片,我在她怀里是那么小巧,她是那么年轻,我立即感到惊讶,母亲竟然老了这么多。我往后翻了翻,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带着模特气质,这是为什么?我似乎发现了秘密,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相册合上了。
在女性里,她算是高个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自然条件”,所以很多同事都称呼她为“模特”。她步子大,走路带风,每天一走进机械厂的大门,看门大爷就会说上一句:“模特来啦。”当然她的特点也不止于外貌,她做起事来也是利利索索,从不拖泥带水。那年春季展销会,车间主任往她手里塞了一份稿子,说是计划有变,书记调任,他得随领导去接新书记,让她代表二农机械厂介绍新产品。她一听,接连推辞,但是没拗过,她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拉着同事说去录音,那怎么来得及,马上就要开始了。会场近千人,她拿着话筒直哆嗦,可是心稳,吐字清晰,语言流畅,就像背下来似的。之后每年展销会都是她作代表。
我去外地上学的第一年,母亲退休了。她心里不踏实,总想干点什么。她请教过别人,退休的人能干点什么营生,很多人说都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在家轻松轻松,没事逛逛街跳跳舞,多有意思。她不这么想。她倒腾过衣服,卖过保险,又去村里村外给人说媒,不过都以失败告终了。于是,她又做起了房屋中介,手里攒的钱租下了一间门脸儿,一卷鞭炮在门外噼里啪啦一放,就开张了。这一干就是13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母亲在外忙还没回家,父亲不经意间和我谈起她的事情,我对父亲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忙活。”我爸看了我一眼,他的脸色随即沉了下来,我感到一丝严肃,他说:“我经常听到外面说她,说她傻,能赚的钱她不赚,我也觉得她傻,傻实在,可是她告诉我,赚了不该赚的她睡不着觉。”我说不出什么。父亲接着说:“你在外地上学那几年,她生病了,没告诉你,那时候我也在忙,没时间陪她,她吊着胳膊,去市里做靶向,一去就是一天,我跟她说过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她没理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听到这儿,我耳根红了,胸腔里像是灌了铅。
去年七一,区影院举办联欢活动,我邀请母亲前去观看。她二话没说,推了手里的活,满脸笑容地答应了我,我有一些不可思议,我在想,她的眼里不是只有工作吗?车行驶在路上,路上的车辆特别多,好像全年的车辆都集中在这一天出来了。母亲看着外面的车流,不由得笑了出来,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说看到这些车挤在这里,想起了之前的一件趣事。在她的房屋中介刚刚开业的那几个月,每天都有人前来询问,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父亲来帮忙。我父亲是个不爱笑的人,遇见谁都是板着一张脸,眉头紧锁,像个要账的。母亲租的那间门脸有十来平米,父亲就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她坐在里面。熟悉她的人们知道她请了一位“帮手”,于是每次来访,都先趴在门玻璃上往里面瞅,如果看见“帮手”在,他们就不进来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的时候他们才愿意进来。结果那天“帮手”早早地回去了,就剩下母亲在里面,她就看到了三五个人齐刷刷地趴在门玻璃上看,那场景滑稽极了。我听着,哈哈大笑,我问她:“那你的‘帮手’之后还去了吗?”她说:“我不让他去了,那天就是我让他回去的,我说他在这儿耽误我生意。”我笑了笑,越笑越笑不出来,我突然想起了那天父亲和我的交谈。我有些慌乱,我在担心她是否早已对我失望,甚至会出现毫无顾忌的责备。母亲的笑容也慢慢收了回去,我看她的侧脸,有些伤感,我意识到我的惩罚即将来临,外面的车越聚越多了。母亲说:“儿子,你在外地上学那几年过得好吗?是不是受罪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鼻腔已经又酸又麻了。就在我担心我没有为这个家做出什么贡献而要受到惩罚时,她在忧虑我的吃饱穿暖。
我打算送母亲一束花,就在她生日那天。我到花店挑选,看了各式各样的花,玫瑰、郁金香、风铃、牡丹、康乃馨、玉兰,没有一束我中意的。我转了转,在花柜的一角发现了一束向日葵,就这么一束,孤零零的。我将它拿起,枝干下端滴下了水珠,花朵盛开的刚好。这是我第一次送花给母亲,心情很复杂,羞愧和兴奋交叠而至。花交到母亲手上时,她笑得很开心,就像那朵向日葵。我们俩人谁也没有说话,都在笑。似曾相识的感觉爆裂了,就是这个笑容,母亲啊,你从未老去,你现在和年轻时一样,绝无二致。我想我找回了相册的秘密,为什么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带着“模特”的气质?因为每一张都有她独一无二的笑容。

张天啸,武清区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青春长篇小说《拆穿:青春的三重梦境》。散文《没有名字的地方》《独特而奇妙的乡村》发表在《运河》。
轮值主编丨许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