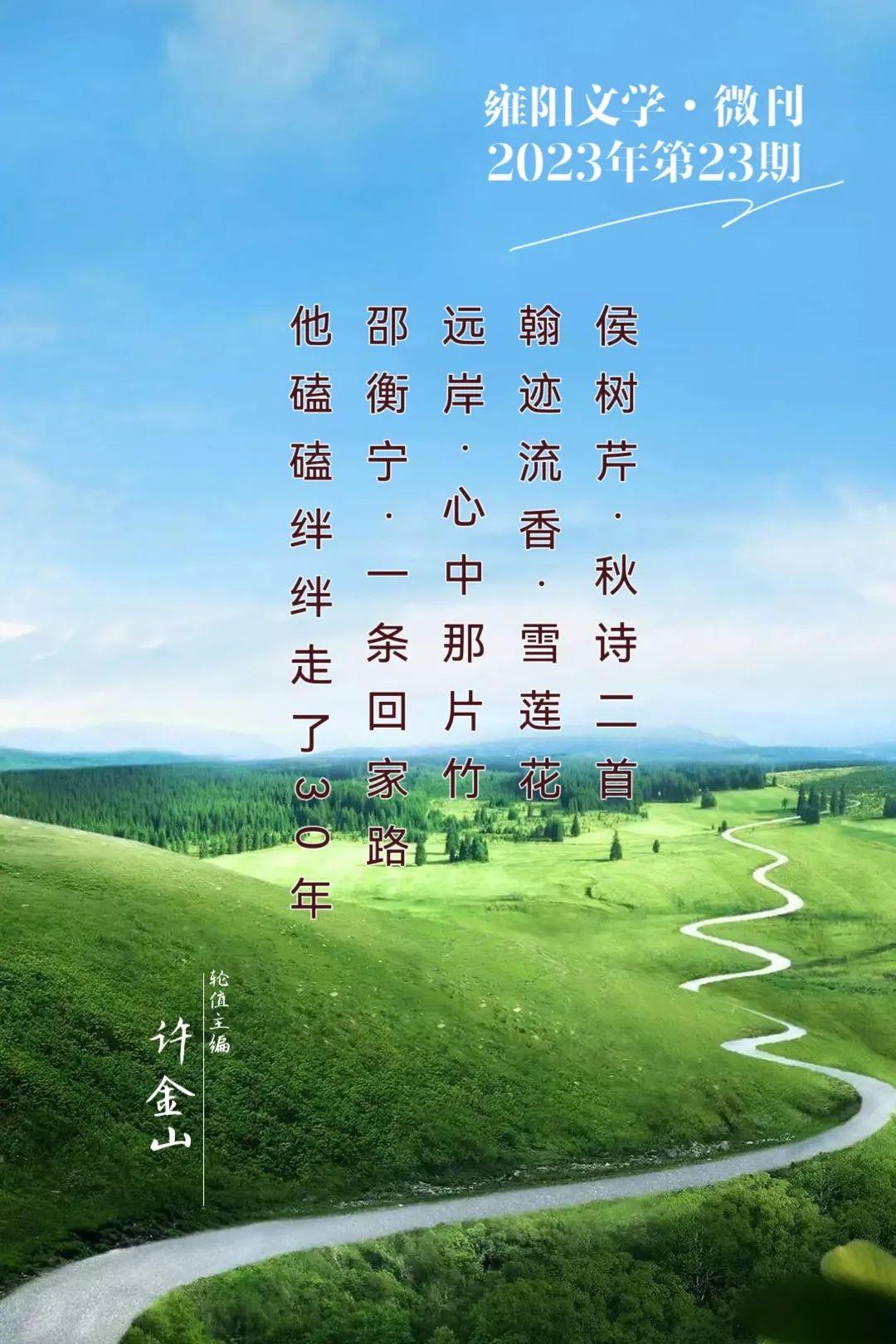
汉诗
蝶衣 | 秋(二首)
1.
时间刚好
你在遗失的蝉鸣里涉水而来
心不染尘,迎风独立
似一枚朱砂痣嵌进秋色眉弯
燃起娉婷,袅娜和光阴的火把
让一条河流开始觉醒
2.
从雁字回时开始
一匹白马就开始铺设时光
四季的轮回里
总有花开忘忧,断鸿声声
赶快抱紧一枚叶子吧
听听叶脉里
是否有管弦独奏,小虫和鸣
在西风又起时
做一枚清扬的雪花
靠近天空

蝶衣,原名侯树芹,武清区教师发展中心教师,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武清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清《运河》编辑。多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发表、获奖,多首诗歌散文发表在天津日报和武清《运河》。其中《白雪之梦》获得鲁黎文学二等奖,多篇诗歌被编入武清诗歌卷。
翰迹流香 | 雪莲花
人们都说
你是上古的仙子
沐浴瑶池时撒落的花
我说
你是天山的冰魄
化作飞笺
镶进雪泥中的魂
人们都说
你是天山上的玫瑰
我说
你如一方的尺素
用那撩人的色彩
绣在天边相思的花
其实 你让我想起了
很远的林中绽放的梅
很远的深谷吐纳的兰
还有
很远的湄岸盛开的荷
不曾暗香 一素的银装
在终年积雪中铸就冰洁
不曾幽静 风霜斗雪中
在寂寞的山腰散发清馨
你不是画脂镂冰的帧卷
春的寒濑
只会赋予你 玉的质地
你不是孤影单只的琪草
山麓下的牧羊人
会为你奏起清远钧天的音律
谁 又见过你如此的温柔
冰凝的贞花穿着云的浣纱
只有那勇敢的雄鹰
才会领略雪胎的容颜
你更不是佛花
却在最高的山巅诠释婆娑
不曾幽咽 又何曾凄美
用香凝的冷韵
吟唱
至美的圣歌

吴翰水,笔名翰迹流香。天津人,汉语言文学专业。作品涉及辞赋骈文,诗词散文。曾获全国诗文大赛一等奖,部分作品发表于国家、省市期刊杂志。
美文
远岸| 心中那片竹
我喜欢竹。但北方少竹,即使去南方旅游见到也是走马观花,留下些许遗憾。于是,走进竹林便成了我多年的梦想。
前几年,区里建成文化公园,里面竟然有竹!于是我经常去那里散步。每每见竹,我便止步观看。花坛里,巨石旁,一丛绿竹茂密葱绿,细长挺拔,惹人驻目。然而,竹只是竹,看也只是观赏,却怎么也感受不到南方山野竹林的天然情趣和诗人笔下的那种意境,体味不出“此处是竹乡,翠绿满心田”的那种感觉,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和惆怅。
一天,我打开手机,是同学发来的一张“竹林图”。我眼睛一亮,正是我心中喜欢的那片竹林!我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放大,凝视画面。渐渐地,那竹就活起来了,一步一步走进我的心田。
竹子翠绿浓密,修长拂云。阳光刚好,风儿正柔,空气中弥漫着清雅的竹香。竹子轻轻摇曳,竹影婆娑,像轻吟,像浅唱。在阳光的映照下,竹节透明,枝叶遮掩,疏影横斜。竹林,或近或远,或浓或淡,或老绿或新绿,绿中隐翠,翠中泛黄,碧里蕴墨,秀色可餐。
竹林的留白处是淡蓝的天,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阳光浅暖,透过竹叶洒下一地斑驳陆离的碎阴,或穿过竹竿斜射过来一道一道细长的光线。天,直连了东方天边的远山。而远山却似醉了的画家,淡墨轻蘸,横划了几笔,若隐若现,神密神奇,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在云天、远山和阳光的陪衬下,竹林愈显翠绿明秀妩媚动人,野趣横生。
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半抱竹林。竹林倒映水中,河水染绿,幽幽地流淌,几条小鱼与水中晃动的竹子嬉戏。河边有几块巨石,或斜或立或平或躺或卧,叠压交错。石旁,几丛新竹依石而生。竹因石而秀,石因水而活,因竹而灵。许是河水的滋润,竹子翠绿,绿的仿佛要流下来,一印就会印在衣襟上。
一条小路依河而成,曲经通幽,隐入天边的远山,山野竹趣远在视野之外。游人三三两两,或与竹合影,或举着手机拍照,或观竹赏竹,脚步轻盈,正合了清雅的意境。小竹桥上,一对恋人,相互依偎,窃窃私语,挽手而去,仿佛听得见小竹桥“吱扭……吱扭”的颤响。
竹林,好美呵!那美,像清爽的小溪水在我的心里欢快地流过,一下一下触碰着我灵魂深处最敏感的部位。我忘掉一切忧愁烦恼,独自在竹的世界里徜徉,不断变幻着角度,想像着竹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想象着晨曦、月色、夕阳、薄雾中竹的摇曳多姿……竹,把山野的情趣点燃,我却把这情趣当酒,与幽竹对饮,吟唱起诗人朱新民一首小诗来:
一拱出地皮儿
尖尖的角就像刺破青天的矛
长高了竟成了姑娘纤细的腰
叶子像裁风的剪
谁知到老做成了扁担
在山里人的肩上颤呀颤
嘎吱 嘎吱
不知是哼着山里小调
还是自我解嘲
颤出了山野情趣
和山里人希望的歌谣。
……
欣赏着“竹林图”,咀嚼玩味着这首小诗,享受着竹韵之美,我浮想联翩。
自古文人墨客偏爱竹,留下了许多吟竹的诗句:郑板桥的“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花不开,免撩花与蝶”;完颜亮的“我心正与君相似,待看云梢拂碧空”;程钜夫的“旧筱斜依石,新梢怒出林”;杜耒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还有,“竹影和诗瘦”“一枝一叶总关情”“直到凌云仍虚心”……
竹,在不同的环境中百般姿态、千般妩媚,文人们则万般情愫妙笔生花。除了赞美竹的生命力强、坚韧、君子、凌寒、高洁、虚心的品格之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竹的故事: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爱民之心跃然诗中;唐寅“欲从节下题诗句,妙在不言不在诗”,喜竹却不忍染墨;王羲之作《兰亭集序》,也是因了“茂林修竹”方得才气横流,落笔如神吧!
南方人善竹编:篮儿、浅儿、篓儿、帘儿、枕、盒儿、竹凳、竹椅等等。竹篾在人们手里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工艺品,体现了竹乡人的聪明智慧和审美艺术。当然,还有竹笋。描写竹笋的诗句也很多。诸如“东君赠我三场雨,笑把千均枷锁开”“春时悄悄赴风约,敢挺琼姿向碧天”“竹笋悄然生遍野,绿衫穿上醉人眸”……如今,北方的公园、城区的景观大道、住宅区、农家小院也能见到竹子,“盆景”也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不仅是因为竹点缀了人们的生活,更是人们追求高雅的精神境界的体现。
我爱竹,一个字——雅!仿佛痴情女子的爱情,竟爱到了“唯君知此意,可与定前身”的境地。
关了手机,惜别“竹林图”,我多有不舍。感谢那位同学知己,让我圆了爱竹赏竹之梦。我想,再去文化公园见到竹,眼里就有了山野竹趣,心境定会大不一样的!
仿佛,我的灵魂也早已幻化为溪边石,娶竹为妻,植于心田,欣赏品味、相伴到老……

袁文洪,笔名远岸。天津市武清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教师,公务员。喜好文学,坚持写作,多篇作品散见省市报刊。作品被中国作家网、天津北方网等网媒转载,入选《现代文阅读》、《作文通讯》,并做为中学生阅读试题和毕业检测试卷。
非虚构
邵衡宁 | 一条回家路,他磕磕绊绊走了30年
他糊涂得厉害。
一条回家路,他磕磕绊绊走了30年,从头发茂密的少年一直走到满头白发。家在哪里啊?他问了别人一遍又一遍。除了想念哥,他狠狠想念的,还有距家不远的那条小河——他年年夏天都在那里洗澡,但他就是想不起家乡的名字,找不到家了。
那些对他来说顶重要的人和事,他分明都记得的:邻居家的大黄狗,老是冲着他“汪汪汪汪”,吓唬他;他还记得小时候哥带他玩,跑过一条小街又一条小街;天热时,钱只够买一根冰棍,哥吃一口他吃一口……从30年前那个夏天独自上街后走丢到今天,他一直朝着家的方向,走了一年又一年,走过了那么多村镇,问过了那么多人,可怎么总也走不到家呢?三年前又黑又瘦的他被送到救助站时,已是满脸风霜,脏污的花白头发下,是一双迷茫又热切的眸子。他说:我想回家!
那个慈眉善目被人叫做“闫队”的人,叫他兄弟。他记不住那人的名字,就喊他“胖子”,还管那个和胖子在一起的人叫“开白车的”,因为总见他开辆白色的车在忙碌。他经常去“胖子”办公室里讨一撮茶叶喝,顺便聊上几句,有时“胖子”他们还会把他的话记在一个本子上。救助站里住着很多找不到家的人,有的被送走或被家人接走了,也陆续有人被送进来。他听人说“胖子”他们都是神探,这些年帮救助站里五千多人找到了家。他也盼着这一天,每天巴望着哥来接他回家,拉着他的手哭,骂他怎么走丢了这么多年,让他好找。
在救助站里住着,吃得饱,还给他治病,没多久他就白胖了不少。他听从安排,每天和几个人一起打扫院子当作锻炼。风起时,落叶不断,他就认真地一遍遍扫。他知道人家帮他找家呢,他想报答。
那天上午他又去找“胖子”讨茶叶喝,只觉得心里格外清明,脚步也特别轻快,走到一棵苹果树下时,有个画面影影绰绰浮现在眼前。他盯着树上的小苹果,忽然想起哥曾告诉他,哥叫卫大平,他叫卫小平。
他一路小跑到“胖子”跟前,很激动地说,这回我能回家了!“胖子”很高兴,说:“你再卖把子力气,接着想想,看还能想起些什么。”接下来的几天里,“胖子”总找他聊,于是他断断续续想起家住淮南的谢村,家里只有哥。那天“胖子”多包了些茶叶给他,“小白车”还塞给他一个苹果。临走时,他伸头看了看“胖子”桌上的本子里记下了一些字。
他把苹果放在床头,勤看着,怕再把哥的名字忘了。他每天都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装好衣物,激动地等着哥来。但,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有天“胖子”告诉他:找到他说的镇子了,也找到了他洗过澡的小河,但查不到他的户籍。所幸的是,在公安系统里查到他哥卫大平的名字,只是哥已人户分离,去了外地多年,目前还没法落实,他得再等等。
又过了一段日子,“胖子”跑来跟他说,通过各种努力,终于联系上他姐了,还有,他86岁的老妈还活着。他有点懵,怎么就把妈和姐忘了呢?
姐却不接纳他,说自己一个人照顾老娘都忙不过来了。他不怪姐,可是真想回家啊,于是泪眼汪汪地看着“胖子”。“胖子”说,我们一起加把力,争取让你回家过年!
那天大雪,“胖子”、“小白车”还有其他几个领导,都乐呵呵地看着他,说要试送他回家了!他激动得嘴唇哆嗦,想笑,又忍不住哭了。他知道,如果试送不成功,他还得回到救助站。
送他走的那天,工作人员为他穿戴一新,还帮他理了发。他一一鞠躬道谢,又和还没找到家的那些同伴们一一握手告别。回家的车上,有3个人陪着他,下了车也一直有人牵着他的手。他怕醒了又是梦,一路上不敢合下眼,忍不住问了一遍又一遍:“这回我真能回家了?”“小白车”笑着说“是”。“胖子”顾不上理他,一路不断打着电话。他听见“胖子”对电话那端说,“告诉在外地的你哥,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把你兄弟送回家了,他这个当哥的得接着!”
他低下头,两手紧张地扯着衣襟。
那个盼了30年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目的地派出所,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妇女花白着头发走进门,和他们一行打了招呼。这个自称他姐的人打量他几眼,阴沉着脸,不情不愿地签了字。“胖子”他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回家的路上,他姐对“胖子”他们说:他青春期时精神分裂,跑丢了几次,家里也努力找过。后来30年过去,都以为他早没了。然后,又开始抱怨,说他哥在外地,把老娘丢给她一个人管……“胖子”开导他姐,每个人都有权利回家,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当地政府。
到了院门口,早已拄着拐杖候在那儿的白发老妈,一把抱住他,一声“儿,你可回来了”,便嚎啕大哭。后又拉着“胖子”手说 ,“我特别感激你们,我的同龄人都先后去世了。我没死,就是等着我儿回家呢,没成想,真等来了!”
进到家里,“胖子”递给他姐几包药,说他有糖尿病,叮嘱每顿饭前提醒他吃。他看到姐的脸色更不好了,想说他会照顾妈和自己,但到底没敢开口,只转过头去打量着陌生的家。
让他陌生的,还有变阔气的镇子和不认识的邻居。那条大黄狗也不在了。他盼得正月都过了,小时和他吃一根冰棍的哥,也一直没回来。
现在,他和妈住在一个老房子里,还有了低保。姐有自己一家子要操持,但每天会过来给他和妈做一次饭菜;他爱吃的水果,姐也会给他买。虽然有时难免会摔摔打打、嘟嘟囔囔,他也不往心里去。他抢着洗碗、拖地,妈夸他把家里的地拖得比宾馆都干净。
妈如今身体还健朗,每天睁开眼看着他就高兴,有好吃的一定想给他留着,半夜会挪进来摸摸他的头,才安心回自己的屋子接着睡。他再也不敢走出镇子了,怕再走丢找不到家,那样妈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有时他也会想念“胖子”他们,他们辛辛苦苦帮他找到家,大老远把他送回来,连杯茶都没喝。记得“胖子”说过,转年他就要退休了,所以他很想哥能回来,陪他一起去看看那些帮他找到家的人,看看那个他生活了多年的地方,对那棵让他想起哥名字的苹果树鞠一躬……
(文中人物“卫大平”“卫小平”均为化名)

邵衡宁,现为某媒体编辑部部长、副总编辑,高级编辑。《记忆被吞噬的母亲》等作品连续12年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国家级,5金3银4铜),获省部级文学副刊奖项若干,并入选多种文集。散文《天津有条滨江道》《玩石子的男孩》等数十篇作品被《人民日报》《读者》《青年文摘》《品读》《散文》等刊发,《我送父亲进养老院》《夏夜听书》《捉知了的夏日》等入升学或中学试卷;《走进幸福大院的失独老人》等数十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被新华网、半月谈、人民号等转发,有的推动问题解决,在新华社客户端一处浏览量在150万至310万之间。
轮值主编|许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