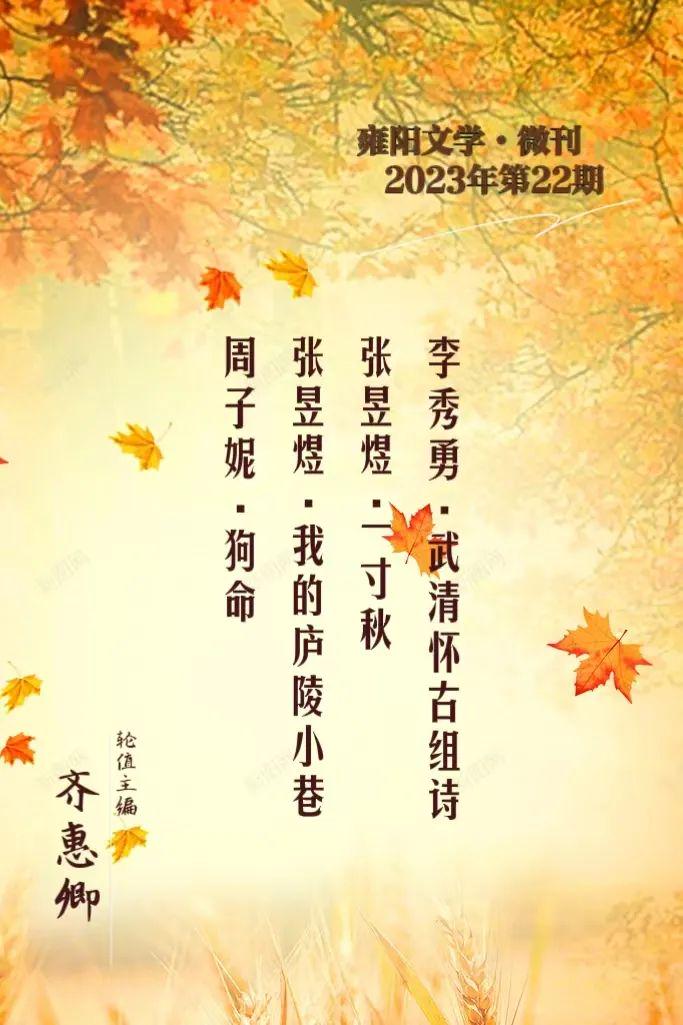
汉诗
李秀勇| 武清怀古组诗
1.七绝•城上
野草荒窠掩古城
当年何事废文明
只今空有遗碑在
欲问沧桑老泪横
2. 七绝•城关
名号城关城不存
曾经盛况了无痕
风光遗落烟尘里
安觅当年旧县门
3. 七绝•大良塔
千年古塔镇东南
永济黎民天地参
一旦坍颓成旧迹
后人无奈作空谈
4. 七绝•祖孙碑
导流济运铸丰碑
二帝英名万世垂
八孔闸前凭圣迹
至今仍觉是传奇
5. 七绝·蒙村
当年水陆动八方
商贾云集生意昌
一夜狂风成梦幻
高台隆起化凄凉
6. 七绝•黄花店
浑河高地遍黄花
辽主疯狂起店家
堪笑当年宫里事
时空穿越到天涯
7. 七绝•鲜于璜碑
一碑出土傲雍阳
复姓鲜于名唤璜
德政化民赢美誉
雁门千载为君强
8. 七绝•十四仓
潞河百里过帆樯
只为京师粮运忙
河务千年成重镇
巍巍十四列仓房
9. 七绝•雍奴侯
名列云台万古传
将军勋绩刻燕然
封侯光耀雍奴地
借寇民碑傲永年
10. 七绝•鼻子侠(通韵)
名冠京津鼻子侠
博文通武爱国家
灭洋除恶弘德义
走壁飞檐谁不夸

李秀勇,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热爱文学,热爱读书,热爱写作,有作品在《天津日报》《天津楹联报》《中国诗词》《运河》等纸媒发表。
美文
张昱煜| 一寸秋(外一篇)
夜,深几许,思绪就厚几分。
都秋天了,还有这么多的蚊子,年逾八旬的老母亲颤巍巍地点上蚊香,敬神一样,把这微暗的“烟火”送到老房子的角角落落,他跟在母亲身后,安心而自在。每一次回家,他总是跟前跟后地护佑着,母亲的腿脚不中用了,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像踩棉花包,陪伴母亲的日子,注定是不多了。
他是母亲四十岁时才结下的“秋葫芦”,小时候,父母把他看得比命还金贵。父亲病逝后,母亲一个人独守在乡下,过着清冷寂寞的日子,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要回来看看,村里人都说他是大孝子。
其实,现在,他的心是最不安的。“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他怕不久的一天,母亲离他而去。
十只小鸡仔在母亲的“指挥”下钻进鸡笼里,鸭子也进圈了,母亲正准备插上吱呀作响的大木门,他笑着说:“娘,今晚的月姥娘多好呀,咱们到院子里看看月姥娘吧。”
在他惠济河边的豫东老家,喊“月亮”为“月姥娘”,多温馨呀。他依稀记得小时候娘教的歌谣:月姥娘走,我也走,我给月姥娘提背篓,月姥娘来,我也来,我给月姥娘去劈柴……他心里念念不忘小时候有“月姥娘”陪伴的往事。
有一年,也是中秋节的边上,是周末,因为周边村子都停了电,打面机用不上,他和母亲只好拉上板车,去县城里磨面粉,队伍排成了长龙,等他家磨好面粉时,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
走到县城的东门口,母亲破天荒地“潇洒”了一回,给他买了七个生煎包子。母亲小心地用四方手绢包着,全递给了他,那次吃的生煎包子,香脆可口的味道,至今难忘。私下里,他认为只有那一次的生煎包子,才是他这半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美味。
“月姥娘”一直跟着他们走,皎洁的月光如水般流泻下来,照着娘清瘦的脸庞,也照着茫茫的四野,泥土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芳香着周身,他拉起板车来,劲头十足。
近了,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尽管树影黑成一大团,传来的婆娑声很是耳熟,还听到几声狗叫,因为有娘在,他是不会害怕的。那时候,娘多年轻呀,走路“哒哒哒”的一阵风。
今夜,又是“秋蝉满枝响似筝”的时刻,他和娘坐在院子的石板上,就着可以佐酒的月光,他又开始劝娘和他一起进城生活了。他和妻子省吃俭用,特意买了个四室两厅的房子,足够大,一家四口住得下。娘苦笑着说:“我都成了一把老骨头了,前辈人常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还是在家好,我的‘大褂子’都油漆好了,哪一天闭上眼,也不怕。我一甩手进城享清福了,留下你爹,咋办,他可是苦了一辈子呀。”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故乡,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月光下的小院子,永远是他难以割舍的心灵脐带,是他最放心又最不放心的地方。
落下了几片石榴叶,声音尽管很轻,但他分明听到了。他向娘聊起当年在地窑子里烧红薯的事,娘一下子来了精神。那也是一个秋夜,干柴燃尽时,娘从火堆里给他扒烧红薯,不停地替换着双手剥红薯皮,看着他吃的满嘴灰黑,娘笑了,他也乐。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日子多快呀。
夜一寸一寸地深,清月照着瘦影,他伏在娘的肩头,聊着开心的往事。忽然,娘话题一转,郁郁地说:“孩,记着呀,给你们买的二十斤土花生,放在东屋的面缸里,你给的钱,我花不完,全放在你爹的大瓷相后面……”他心里隐隐一疼,眼泪唰地流了一地。
我的庐陵小巷
小巷悠悠
没有诗人笔下的丁香花
也没有撑着雨伞的姑
有的是心头的淡淡清香……
水巷、仓口巷、竹笋巷、保太巷、珠紫巷、九曲巷、莱菔巷、衽席巷、孔家湾巷、世兴庙巷、西肖家巷……苏轼眼中“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的吉安,到底有多少条小巷,我不得而知了。想约几位好友拍一拍吉安的小巷,他们说新开发了不少商品房,修了大马路,很多巷子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作家陆文夫在苏州度过了六十多年,读者眼中,他和苏州早已融为一体了。尽管吉安不是我的故乡,但在这生活了三十多年,连卖菜老婆婆的吆喝声都听出了亲切。我想让心灵跟上脚步,寻找和亲近小巷,以求内心的慰藉。
从大榕树向后河方向下行,穿街过巷,最先看蓝底白字的路牌——保太巷,正如一位淡定自若的老人,在静静的岁月里幽居。旁边的新房争着抢着彰显“时尚”和“伟岸”,这些与我无关,与悠远的巷子无关。就着冬日的阳光,慢慢地,穿越古巷,慢慢地,翻阅古巷,忽然觉得,巷子就是自己的啦!
石头垒砌的院墙沁着枯黄的苔藓,柚子树从墙里探出头,两排杉木店面,温暖而孤立地泛着褐色的光。门头处,有讲究的人家挂上小圆镜、剪刀和柏树枝,以求避邪和祈福。尽管有些店面向后倾斜着,但丝毫不影响商家的经营。每一处早上开启、傍晚又合上的门板,吱吱呀呀地数着日子,似乎想把眼前的浮躁兑换成赣江的渔火点点,清风徐徐。
踩着大块的石板路,我想把流失的岁月与现世的繁华对接起来,可是,行走在小巷深处,那风烟俱净的时光,那不染纤尘的气息,让人忘记了世间的喧嚣。
一个卖藤制品的门面,黑且旧,上上下下挂满了各式各样藤制品,精湛的手艺,是生活,更是艺术。藤器与光阴叫着板,让人心生怜悯。旁边,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排档,问彭老板开这排档多少年了,他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呵呵一笑说,掐头去尾十五年了。发好的米粉,团好的碱面,安静地簇拥在竹圆箕里,一个窝窝头大小的竹笊篱,泡在翻滚的大锅里,搅拌着最地道的原味生活。
来一碗碱水面!多放点香葱!好勒!
热腾腾的碱水面端上来了,小木桌有了生机,左手边是小醋瓶、右手边是半碗辣椒酱,添加自便。冒着热气的面,在清清的面汤里“荡漾”开来,猪油夹带着葱花的香味,直袭鼻尖。
念念不忘碱水面才两角钱一碗的时候,凝白的猪油在滚烫的碗里融化的一瞬间,香,真香。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年青涩的小女生已到中年。此刻,悠悠我心,在往昔和现实中穿越,呲溜呲溜吃着劲道的面,咕嘟咕嘟喝着滚烫的汤,舌尖上很是满足。
吃完面,踩着高低不平的水泥路,我又找到了一个小型蜂窝煤加工厂。多年了,蜂窝煤做饭取暖已淡出我们的视线,但今天看到,仍是亲切。那咣当咣当的声音,怕是赣江水和古南塔都听得清清楚楚。
午后的阳光把离街市最近的九曲巷照的暖烘烘的。稻子米果的小摊子旁,围了三四个细伢子,他们头碰头,看着滚上豆粉的米果新鲜出炉。一个穿着旧军装的摩的司机,半躺在摩托车上,在百无聊赖地等客。头戴鸭舌帽的老伯,细心地炸着串串香,五个一串,用竹签串好,风穿过小巷,那浓郁的香味,飘得很远。
小巷在冬日的阳光下安静地打坐,走几步,遇见补锅底的老阿姨,戴着老花眼镜,端坐在铺子前,在一锤一锤地敲打着钢精锅底。店铺不需要招牌,脚边的白铁皮、一个个烧黑的锅底,胜过招牌的威力。两只公鸡在捡拾着地上的瓜子壳,旁边,一位头戴绒帽的老婆婆,同样是戴着一个老花镜,系着蓝棉布围裙,围裙下面,是一个竹编的小火篮,老婆婆仔细地纳鞋垫。她们各自忙碌着,许久都没有抬头,轻声聊着身边的大事小情。
老婆婆面前摆着小方凳,上面放着玻璃瓶装好的酒药,烟盒大的纸片上写着:祖传甜酒药,五角一个。老婆婆多少岁,八十岁抑或是九十岁,脸上的皱纹和老年斑,似乎告诉来往的人们,自己陪着小巷的时间最长久。在花白的头发上抿一下针,接着,顺溜地扎进鞋垫里,一下、两下,背面,正面,针尖翻来覆去熟悉地牵引,长长的棉线划出优美的弧度,恰似岁月的低吟浅唱。
散发着儿时味道的小巷还在,弹棉花的、打铁的、做秤的、画瓷画的、织渔网的铺子还在,心里突然生出太多感动。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晨昏迭更,我在这里,陪着小巷,小巷也陪着我。那窄窄的小巷,以人间的烟火为底色,守着嘀嗒作响的时光,书写着浓浓的庐陵古韵,让人回味绵长。

张昱煜,女,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书香三八”读书活动特约作家,散文、小说、诗歌多次获奖,有作品被翻译成俄文、韩文、阿拉伯文等。
小说
周子妮 | 狗命
苇坑当时还不叫苇坑。它躲在院墙坍圮的角落里,看着一个个狰狞的面孔在家里窜来冲去,一会儿掀起那个,一会儿砸烂这个。那个领头的喊:“这是德国牧羊犬!是一只狗间谍!母间谍还下了一窝小间谍,给我砸!”正在厢房里追着猫儿黄黄玩的苇坑逃过了一劫。待它跑出屋子,看到了兄妹几个全部都被剥了皮,一个个粉红色的小肉体都挂在树上被吊得细长。它的妈妈被压在了一堆砖头瓦砾下,只露出了后腿和尾巴,黑色的毛发被风吹得颤颤巍巍。苇坑夹紧了自己的尾巴,身上黑短的毛抖得跟筛子似的,它被吓坏了。
老杨树的叶子在风里吟着哗啦啦的挽歌,苇坑一动也不敢动,连喘息都是小心翼翼的,直到年轻的主人钟鸣木呆呆地走进院子,他好像没看到老杨树上新增的“挂饰”,只是直直地走到井边坐了下来。苇坑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围着钟鸣的腿转了一圈,又把前爪搭在他棕灰色的长裤上,讨好的伸出舌头舔他的手指。钟鸣终于注意到了苇坑,他把它抱在胸前,苇坑发出了呜呜的叫声,那“呜呜”声里有它的妈妈是怎样被砸死的,它的弟妹们是怎样被吊在树上的,钟鸣发现自己的长衫湿了,原来狗也是会流眼泪的。
他们离开了苇坑胡同的宅院,来到了一个叫雍泉的小村,苇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叫苇坑的。它很想念苇坑胡同的院子里老杨树叶哗啦哗啦的声音,想念厨子老王顺手扔给他的猪下水,想念和猫儿黄黄追着玩。它想家,想妈妈。主人钟鸣不爱与人说话,旁人也不爱与他说话,苇坑更不讨喜,人们都说它是资本家的狗尾巴。但淑娟是个例外,她常给钟鸣送菜饽饽,还帮他洗臭烘烘的汗衫,虽然钟鸣总是对她说:“淑娟,你不必这样。”
组织上来找钟鸣谈话,说到个人问题,他更不愿吭声。他只是比以往更沉默,下地做工都躲着人走,更躲着淑娟。淑娟的住处距离钟鸣只隔了一条窄窄的土路。那个傍晚,钟鸣回来发现自己出工要穿的汗衫、解放鞋全都不见了,料想是被淑娟偷偷拿去洗了。趁着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他快步往淑娟家里走,天黑再去,被人看见就说不清了。苇坑一路小跑地跟着他,进了门发现只有淑娟自己在家,桌子上还备了酒菜。苇坑隐约闻到肉的香气,一个劲儿地往炕桌上窜,淑娟破天荒地摸了摸它的脑袋瓜,用瓷盆子装了几根鸡骨头放在了院子里,苇坑兴奋地摇着尾巴把头扎进瓷盆里大嚼特嚼。正值初秋,明晃晃的月亮挂在梢头,房屋后的天像是冻结了的湖,冰冰蓝的挂了几颗晶亮的星。苇坑好久没有吃得那么酣畅了,它把前爪按在地上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打了个滚后卧在地上盹着,睡眼朦胧中它看见淑娟家的窗帘不知什么时候拉上了,窗帘里透出暖黄的光和天上的月亮一样。
苇坑醒来已是凌晨,它听见了门被吱呀一声推开,钟鸣出来了,它睁着惺忪地眼跟着主人回家。进了门,它看见钟鸣从立柜里掏呀掏,身子几乎都要埋进去了,终于扯出一个青白色的布袋子来。钟鸣拎着布袋来到了院子里,又点燃了几根木柴生了火,苇坑怕火,躲得远远的。它看着主人倒出了许许多多的纸片片,仿佛是一些信,还有照片。钟鸣一张一张地拿起那些纸片,仔细端详一番,又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扔进火里。在晨风中,火舌越来越高,青色的烟雾升起来,苇坑看见钟鸣用手遮住了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月亮变得淡淡的,天色还如冰冻的湖泊一般静谧,只是已经是早晨了。
转过年,淑娟生了个大胖小子,叫平安。钟鸣整个人都喜气洋洋的,大家都说钟鸣当了爹,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听着都有底气了。但淑娟开始越来越不待见苇坑:“怎么回事?怎么又把它给放进来了,狗脸狗脸,翻脸就不认人,咬着儿子怎么办。”淑娟说着,脱了脚上的鞋冲着苇坑扔了过去。苇坑识趣,顺着门缝一溜烟跑走了。从此,只要淑娟在,苇坑半步都没有踏进过屋子。
春去秋来,转眼平安三岁了,旁人家的孩子早就会跑了,平安却还走不利索,说话也只会咿咿呀呀。钟鸣不放心,借了个板车抱着平安去了医院。那是钟鸣和淑娟第一次听说“唐氏综合征”这个名词,大夫讲明了所以,淑娟险些晕了过去。那天晚上,苇坑看见钟鸣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灰白的烟灰啪嗒啪嗒地落在了地上,让它想起苇坑胡同的老杨树春天时的飞絮。天将亮的时候,钟鸣掐灭了烟走进了屋里,抱起了还在熟睡的平安狠狠亲了两口,他的泪又来了。
平安慢慢长大了,苇坑却几乎不敢在家里露面了。淑娟不知从哪里听说狗身上的细菌会导致胎儿发育不全,从此便狠毒了苇坑。只有在钟鸣在家的时候,苇坑才会在院儿里停留片刻。这阵子,钟鸣总是心事重重的,他听说很多和他一同下乡的知情都返城了,雍泉距离北京不过百十里地,他心里的火“轰”地就着了起来。他又变得沉默起来,沉默中还带着一丝神秘,他常常一个人伏案到深夜,笔耕不辍地写着什么,偶尔出去解手,他会朝着苇坑会心一笑:“苇坑,咱该回家啦。”
那天夜里闷热得惊人,淑娟哄着平安先睡了,钟鸣又一个人伏在案头上不停地写。夜真黑啊,月亮都热得不愿出来,钟鸣越写越兴奋,苇坑却突然钻了进来,紧紧地夹着尾巴不住地吠叫。淑娟和平安都被吵醒了,苇坑咬着钟鸣的鞋子往屋外拖,钟鸣被苇坑的突然袭击搅得心烦意乱,脱了鞋拍了一下苇坑的头。苇坑的眼睛由黑变红,浑身的黑毛都竖了起来,它紧夹着尾巴窜上床,朝着平安圆滚滚的胳膊咬了一口。平安歪在床上哇哇大哭,淑娟看了看只有一道浅浅的口子,便披散着头发跳起来,抄起墙角的铁锨就朝苇坑身上打。苇坑疯了似的跑出去,钟鸣担心淑娟把苇坑打死了,抱起了坐在床上的平安也追了出去。在宽广的黄土地上,淑娟一锨子就把苇坑拍在了地上,它老了,早就跑不动了。在钟鸣赶到时,淑娟给了它致命一击,他听见苇坑又发出了像幼年时的“呜呜”声,渐渐没了气息。
突然之间,远处的天好像划过一道血红的光,大地开始剧烈的颤抖,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周子妮,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意林》《微型小说月报》《岁月》等。该作品发表于《微型小说月报》2023年第4期。
轮值主编|齐惠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