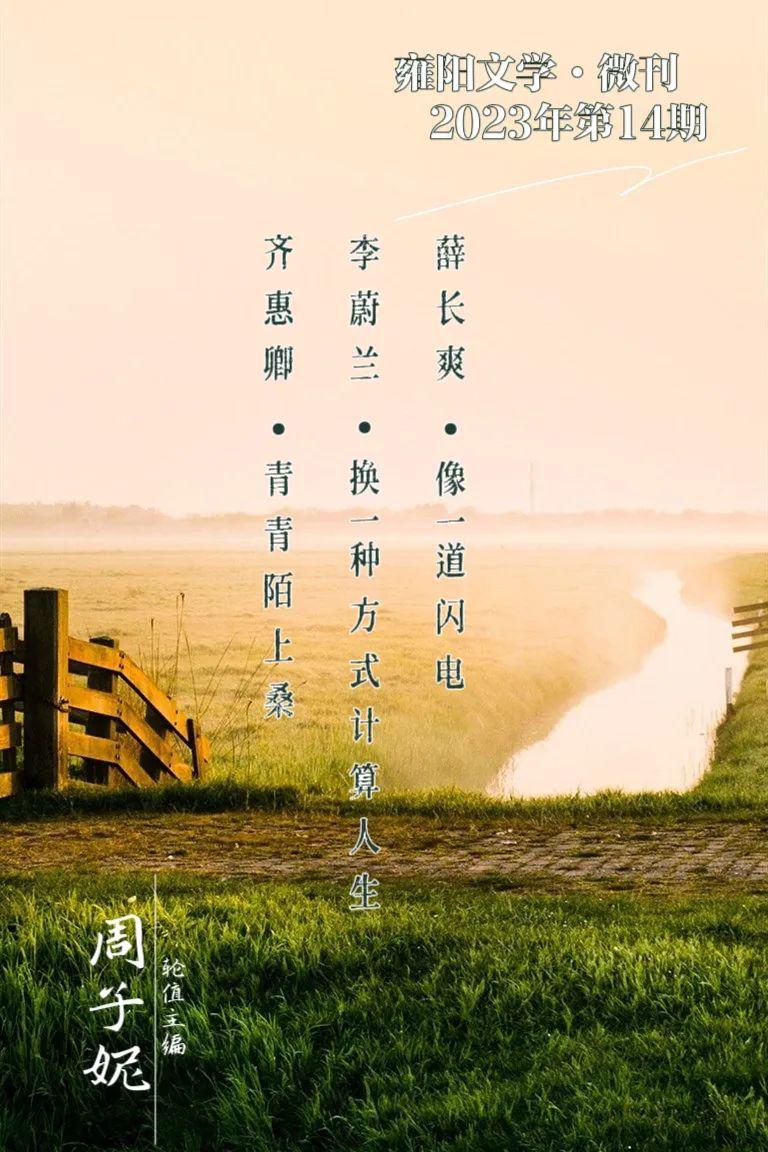
◉汉诗
薛长爽 | 像一道闪电
一道闪电在身后追来
脚下路面的坑洼,片刻之后
会被暴雨填满
小孩子在跳,在喊
想拽住闪电的尾巴
骑上去,拖出一道虹
妆点童年
年轻人躲到了公交站廊下
望着车来的方向,颤栗的双手捂着包包
生怕一道立闪,照见
里面瘦弱的日子,点燃
陌生城市的孤立无援
我不喊,也不躲
与它静静对视
等待被闪电撕开的
云缝里的蓝天
就像有些梦想、有些爱
经年累月,变得不能再骨感
还有些人、有些事
和路边上了锁的咖啡屋一样
或变得遥远,或已走出时间
却像一道道闪电
在黑暗中一次次骤亮
让前行的路,不孤单

薛长爽,1972年生人。自一九九二年至今,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有《青春组曲》《习惯有你》等多篇诗歌、散文在天津市“文化杯”“中仓杯”和武清区各类征文比赛获奖。另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
◉美文
李蔚兰 | 换一种方式计算人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一次华美落幕了,当谜一样的一本、二本分数线即将揭开它神秘面纱的时候,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分数好的,在考虑如何填报理想的志愿,分数差的,在考虑是复读还是托门路。高考结束了,看着去年高考状元的照片,看着他们那疲惫的脸庞上厚厚的眼镜,不戴眼镜的面无表情,没有青春的朝气和飞扬的神采,有一些心疼和悲哀。知道他们实在是太累了,十年寒窗苦,一朝蟾宫折桂,他们是胜者,日后是否成为王者,有谁知道呢?据说有人做过考证,几十年来的高考状元并没有很杰出的人物,我不敢妄加指责这是高考的悲哀!
我很欣赏一句话:“人生就是总合力”。是不是很富哲理?当然不是我说的,它出自一位生活极为困顿的日本乡下老婆婆之口。
日本喜剧泰斗、著名作家昭广8岁时,父亲死于广岛核辐射,母亲只好将他寄养在佐贺乡下的阿嬷(外婆)家。那里只有一间破烂的茅屋,但却是昭广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日子穷到极限,但是乐天知命的阿嬷总有神奇而层出不穷的生活绝招,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丰富了昭广的心灵,也让家里随时洋溢着笑声与温暖……
破败的茅屋前是一条宽约8米的河,上游有个市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顺着河水漂流而下,阿嬷用一根木棒拦截住漂流物;树干、树枝晒干当柴烧,“尾部开杈的萝卜,切块煮起来味道都一样”,“弯曲的小黄瓜,切丝用盐拌过后味道也都相同”。阿嬷说,这条小河是家里的免费超市,连送货都是免费的哦,只是不能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啦。阿嬷出门的时候,必定在腰部缠上一条拖着磁铁的绳子,吸到的铁钉、铁屑,装满桶子后拿去卖,贴补家用。阿嬷是学校清洁工,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去打扫,先是厕所,然后才是办公室。“你做完辛苦的工作,后面就会觉得是天堂了。”
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书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情节:昭广的成绩一直不好,每门功课总是考1分、2分、3分。当昭广把成绩单拿给外婆,小声说:“对不起,都是1分或2分。”“不要紧,不要紧,这些加起来,就有5分(5分是满分)。”“啊?成绩也可以加起来吗?”昭广吃惊地问。阿嬷表情认真,果断地说:“人生就是总合力!”
好一句“人生就是总合力”,好一位善于用加法计算人生未来的老婆婆!在她的人生字典中,没有“哀愁”、“抱怨”、“绝望”这些词语,坚强地挺起不屈的脊梁,面对困境,不哭天抹泪博同情,不咬牙切齿恨不公,而是面带笑容地“接受、改变、度过”。昭广与外婆一起生活了8年之久。在开朗、乐观、智慧的外婆那里,昭广学会了一个人如何微笑着面对艰苦和挫折,懂得了快乐人生的真正含义和计算幸福生活的窍门。
看完这个故事,我把话题再回到高考上。人生不只高考一条路,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生的规划和态度。我们必须明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走金榜题名式的成功之路。
高考只是人生中一场重要的考试,高考的好坏也不能决定人一辈子的命运。
古往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未通过“独木桥”的比比皆是。李白功名未得却诗篇不朽,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发明大王爱迪生、成功学大师卡耐基、文学大家沈从文、政界巨子丘吉尔、数学大师苏步青和著名作家三毛的成长和成才的经历,告诉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努力站在自己热爱的行业的巅峰,也可以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成为一代伟大的人物。人生就是一个大考场,生活就是一道道考题,就看你如何去把握,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一次次不成功的考试去获得“人生的总合力”,进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换一种方式计算人生,就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认真书写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答卷。

李蔚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武清文联副主席,武清《运河》杂志主编。作品散见于《中国文化报》《今晚报》《天津日报》《人民文学》《天津文学》《散文》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寂寞烟花》《艺苑探幽》《牵住生命的太阳》等。
◉美文
齐惠卿 | 青青陌上桑
我们有很多平坦、整齐的土地,站在河岸上抬手往东一指,喏,那都是。你掰着手指算一算,那样的土地恐怕五亩不止,十亩不止,或者百亩千亩都不止吧。那里种着许多的庄稼,有高粱、有小麦、有玉米、有大豆;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杨树、槐树、柳树、椿树、桃树、葡萄、杏树之类,桑树也一定要种的,因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见,桑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就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因为,桑与麻同为古代人们解决衣着、温暖躯体的最重要的植物,所以桑麻一肩并肩地站立,就被指称为农作物和一切农事活动了。但是,不管古人怎么抬高桑树的地位,父亲却都没把它当作主要的树来种。他在那条横亘在村庄和河流之间的长堤上植一片白杨,种一段柳,再培一段椿树,桑树却只做为一种陪衬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堤坡之上,也把它们种在通往田间的道路两旁,除此之外,我们的所有的土地都再没有桑的一点位置。
属于落叶乔木的桑树,虽不如杨树、柳树高大,但也不是矮小的灌木,终是能长到几米高吧,它们的主杆长到和我们的胳臂腿一样粗细时,也只是仰望着高高河堤上的白杨和柳树,就跟我们敬畏地抬头望向大人们的脸庞一样。
那条陡直的大堤,倾角足有七八十度,夏天的暴雨将堤坡冲出一条一条的沟痕,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不想走通往河堤那条路,就顺着雨水冲出的沟痕往上爬,在那里玩半天,浑身就都是泥土了,活像个泥猴。夏日渐近,桑树吐出叶芽,一片青云绿雾,不久就挂了果实,待果实红润,人们将低处的树枝一扬手拉住,然后摘下一颗颗熟透的桑椹,顺势放到嘴里吃掉。就这样,果实越摘越高,越摘越少,直到人们用什么工具都再也够不到了。够不到的美味却成了最后的诱惑,我们为了能吃到那最成熟的几颗就会不顾危险,爬到树杈上,拽到一根带果子的树枝,一跃把自己吊在上面,一手抓住树枝,一手摘桑椹,危险的举动有时让我们尝到甜头,有时就会自食苦果。
我的童年很有些淘气的功底,能与温顺听话的孩子为朋,也能和淘气顽皮的孩子为友。一边不断生病,一边又不断地弄出意外伤到自己,因此没少让父母担惊受怕。或者,正是因为隔三差五地生病,时常躺在炕上不能和小伙伴到外面去玩,所以一旦身体好转,就往外跑,似是要补回因病而耽误掉的玩耍时间,而母亲又希望我的身体快快强壮起来,所以,除了不让我亲近所有的水源,对我的一切活动都很少禁止,即使是伤了碰了也只心急火燎带着我去看医生,而很少受到她的责罚和打骂。
那是一棵青年桑,虽是种植的年头不长,那一年它也结了果子,随时成熟的果子被人们顺手摘走,最后只剩下高处的一些诱惑着我们。为了摘到高处的那些,我勇敢而又冒昧地攀上树去,这次可没往常那么幸运,我从那条树枝上一下子就摔到堤坡上,结果是两颗前门牙松动,满嘴是血,导致母亲心疼了很久,后来母亲每想起,也还伤心不已。虽然这件事很让我丢面子,但也并没记取教训,也没见了桑树就跟仇人似的远远地躲着走,只是,后来渐渐大了,再也不会去爬树,而是喜欢仰望一棵树,望着它们茂密的树冠、树叶,时不时地发会儿呆,想一会儿关于它们的陈年旧事。
在乡村,极为罕见的是张家人爱养桑蚕。每到春天他们都弄几个大竹筛子,摘取嫩嫩的桑叶撒在筛子里,放养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桑蚕。桑蚕在里面蠕动着吃桑叶,能发出一种“沙、沙、沙”的声音,极像在下一阵阵淅淅沥沥的雨,久久地、久久地都不停。望着那一筛筛的桑叶和桑蚕有时候会想张家人是怎么从高高的桑树上采到桑叶的,那么高的树呢,采叶之人是不是很吃力才能采到?这又不似江浙之地,有七八尺高之桑,不必登梯爬树。但是,也从不去问张家女儿,虽然我们无话不说,但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没有私田的年代也许是隐秘的,我怕畛域之外那高大的桑树叶子摘掉的过多会是一片惨景,而影响了树的生长,但每回看到路边的桑树,也没见哪棵叶子少得有碍观瞻,那么我只能让我的问题成为历史。舌尖之下不追不问不让人家难堪也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吧。她们家那几个养着桑蚕的筛子时常被人们搬来搬去,张家奶奶有时见我们过去,也热情地把它们搬到炕上来让我们看新鲜。桑蚕在桑叶间如翻山越岭般艰难蠕动,做着一项古老的被人类有效利用的工程。而蚕并不知道这项工程让人类利用了,它们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地工作,态度也总是那么得意、从容、优雅,它们从一片叶子到另一片叶子的漫长的旅行,并不会因为有人观看就显得惊慌失措,更不知道要顺从人意如猫狗类看人脸色,可见蚕茧对外界的意识麻木,只是蚕屎不时从筛眼里漏出来,在炕上和地上的就落了一些黑黑的如米粒一样大小的东西。看着蚕宝宝在里面吃桑叶,肚子变得又青又大,不久就吐丝,拉成一条长长的细细的丝线挂在一片片桑叶上,好像要把自己织到里面不出来了,不久这些蚕宝宝就会钻进蚕茧里。
宋应星说蚕茧壳外面的浮丝可用纺锤打线,织成湖绸。织得成湖绸织不成湖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成线就可用于女红了。而剥掉浮丝以后的蚕茧的处理方法则不会是那么简单,想必张家人轻易不会自己做这事,因为那是一条非常繁琐的、技术含量极高的工艺流程,不是几个筛子就能解决的。其实,至今我都不知道张家最后把蚕养到了什么程度,那些蚕茧怎样实现了最后的价值?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张家的女儿远嫁他乡,我再没去过她们家;只是偶然听说,张家的母亲操劳成疾过早去世,张家父亲二婚,却没人提到她们家是否还养蚕不养蚕。
父亲种桑树,却不养蚕,他只把有关桑树和桑蚕对于人类极端价值的宣传画贴到墙上,那便是桑喂养了蚕,蚕吐丝成茧,薻丝成绸,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五十衣帛的来路,其实也顺便宣传了植桑造林,美化环境,水土保植的思想。我时常对着那幅宣传画发呆,是因为那上面有一匹匹精美的丝绸,被一件漂亮的圆环挽起,尾部成帷幔状铺散开来,就想着它们要是真能做成一件件衣裳,至我知天命之年穿上,还真是不错。那时候,小粗布都不多见,何况丝绸乎,可见我一直有在困境中遥望未来的态度,那便是心怀高远、不屈不挠。
做着这样的理想梦再回头去看,忽然发现,父亲种桑及张家养蚕都只限于事物发展的最简单和最原始阶段,与那些高科技的柔软的丝绸挂在衣柜里却要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光阴,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也不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父亲从不大面积植桑,张家也从不把蚕养成气势,只是小打小闹着玩儿,或者说,就是为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让日子多生出一层厚重的味道。
在我们楼房的拐角处,有两棵桑,一棵男桑,一棵女桑。夏日里,桑树大大的树冠比过一顶大大的太阳伞,风透过树叶吹下来是凉爽的,这时男桑下坐着闲散的带着孩子的人们,因为男桑下的土地很干净,不会时时摔裂一颗颗桑葚下来,弄脏人们的衣服;而在道路另一边的女桑下,时常有弯腰拾桑葚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时候他们也会带着一个孩子,捡那些没有摔坏的桑葚。桑葚的味道极清淡,人们来捡,是因为这些桑葚是难得的纯绿色果实吧?他们匆匆捡着,觉得够用了就又匆匆走掉,留下一地摔烂的桑葚。那棵桑树下大半个夏天都是紫黑色的,直到树上的桑葚没了,再下几场暴雨,地上才干净了。每年冬天叶子落净,再来看这两棵桑树,就觉得它们像极一副老人的筋骨,扭曲、盘结、干硬,似是老的无法再老,也才赞叹古人费心造词——沧桑,是那么精准和恰如其意。而所谓沧海桑田,是指世事变化,经历的多了,就是沧桑。
其实,桑并未经历什么,只是它的样子貌似,被有心之人借来一用。不过桑确实让人踏实,让人心有所依,体有所属。这也是为什么古人说桑是中央之本的缘故吧。

齐惠卿,天津市作协会员,武清区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辽河文学》《散文海外版》《青海湖》《运河》《天津日报》等报刊。著有散文集《那时桃花源》。
轮值主编|周子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