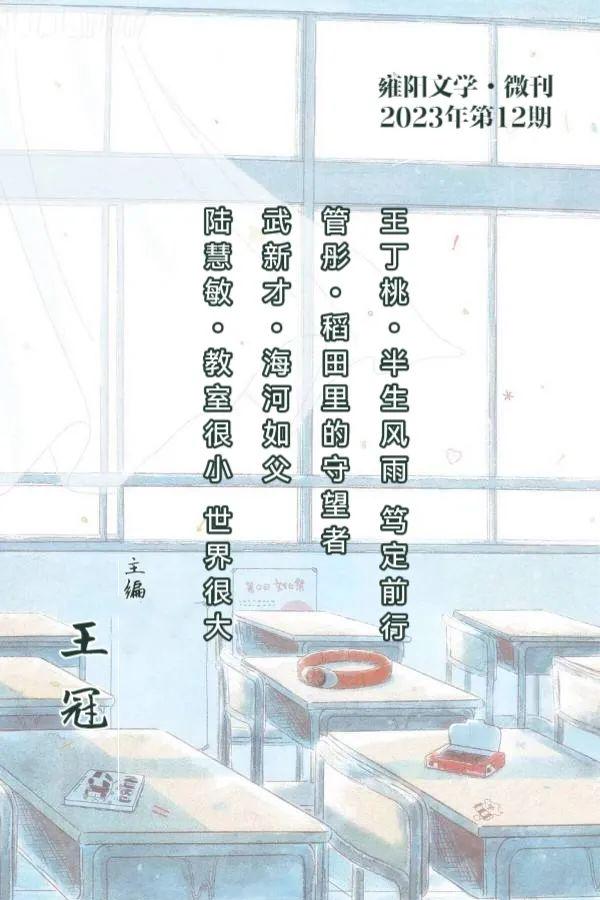
◉汉诗
王丁桃 | 半生风雨 笃定前行
半生风雨,开始思索
思索渐行渐远的青春
思索顾此失彼的友谊
思索事业的持续前行
思索爱情的涟漪平静
思索子女的聪明灵动
思索双亲的照顾陪伴
思索自己的价值观
世界在进步
现实在变化
山路和荒野
映照在前进的道路上
烟火和星光
流连在路边的风景中
在成熟的外表下
那颗看似年轻的心
一直想跳跃
半生风雨
我会一直笃定前行

王丁桃,北京媒体人,历任法制日报、中华新闻报、中国网中国视窗、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大数据与科技传播委员会编辑、记者、副总编、副主任,曾参与编辑出版《全国法治宣传书画作品选集》《全国新闻工作者书画作品选集》《跨阶层行走新闻作品选集》等。
◉美文·新人
管彤 | 稻田里的守望者——袁隆平爷爷逝世两周年有感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爷爷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转眼间,袁爷爷离开我们已近两年。两年间,每当研学时看见稻田,每当端起饭碗,看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个辛劳的身影便浮现在眼前……
回望童年,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弄清楚,“袁隆平”这个名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刻进脑海里的,那个时候只知道,他对全世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来上学了,他总是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教科书上,老师们的口中说出他的名字时也满是崇敬。年龄再大些,自己上网了解到,是他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不再挨饿,让贫瘠的土地结出沉甸甸金黄,让属于幸福的稻香飘满整个世界。
可是,2021年的5月,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感到我坚实的心墙被抽走了一块砖,冷风瞬间吹了进来……
电影《寻梦环游记》有段台词这样说道:“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社会上不复存在;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不再和你有关,从此以后不会有人知道你来过。”第一次与第二次死亡,对于仍然存在的人来说是一种伤痛,但永远将不会来临的第三次死亡,是对袁爷爷付诸一生去实现梦想的回答。等到我们这一代人有后辈时,会有人向他们介绍:袁隆平是一个把一生都倾注于造福人类的人,他或许并不高大,但他伟岸;他或许只是个普通人,但他伟大;他或许对自己很吝啬,但他对人们永远无私地奉献;他或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但他使得无数人安居乐业……
袁爷爷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袁爷爷正是如此:一生躬耕于田野,淡薄名利、坚定信念,如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
迈入耄耋之年的他,本应“颐养天年”,却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对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他是映在眼底的阳光,世界不能没有太阳;对能吃饱饭的国人来说,他是生长在内心深处的善良,人应永远心存感恩;对面临质疑的中国来说,他是融入血液的骨气,使国人敢于坚挺起脊梁;对失败受挫的人来说,他是干涸的大地上流过的涓涓细水,不慌不忙地带来希望……
一生守望稻田的袁爷爷,把稻香送给了全世界。他憧憬着禾下乘凉的美梦,希望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希望全人类都能吃饱、吃好。
如今,袁爷爷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他的梦想,已经驻进了14亿中华儿女的心里,他奔走在稻田间的清晰脚印,正在指向遥远的未来,迈向我们美好的新时代!

管彤,武清区杨村第三中学高三学生。
◉美文
武新才 | 海河如父
岁末年初,一部记录海河流域生态人文的六集电视片《海河》的播出,给极不平凡的2022年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成为迎接2023新年到来的“贺岁大片”。
最早认识海河,应该是孩提时代,在边远偏僻的太行山区小山村里,高音喇叭说,“一定要根治海河”。至于海河是什么样子,具体在哪里,大概方位只知道在天津,为什么要治理海河,不太清楚。一九六三年,我出生后的第一年,根治海河开始了,持续大约十五年,直到1980年才告一段落。
我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参军入伍的,到我所在的部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八师时才得知,我们师这次的任务不是抢修铁路,而是参加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史称“引滦入津”,就是把河北滦河甘甜的水引入天津海河,解决天津人民吃水难题,这样又对海河有了新的感知认识。
天津号称“九河下梢”,也就是说有九条河流入海河、南北运河等,汇聚在三岔河口奔流到渤海,如此庞大的水系,难道供不起当时只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生活用水?号称天津人民的母亲河——海河难道断流了吗?
这样奇怪的想法也是当时对海河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积累,尤其是在观看了大型生态人文纪录片《海河》之后,更加深了对海河流域的了解。
上世纪开始,天津人断断续续地喝着又苦又涩的咸水,这座当时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长期饱受着缺水的困扰。
众所周知,海水是咸的,如果把海河、南北运河等汇为一体,水同样没法喝,这就造成了守着大河大海却没有水喝。治理海河并没有解决天津人民吃水困难的问题,于是,便有了“引滦入津”。这样一来,我也彻头彻尾成了地道的“天津人”,通过工作见证了海河流域的变迁。
一九八二年初,在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景忠山脚下,我们铁道兵八师承担了“引滦入津”最为艰难的一段工程。为了把原计划三年完成的隧道工程压缩至一年半,我们全体指战员真是拼了。
夏天,在潮湿的隧道里开挖,当时没有先进的工具,全靠人海战术。在出石渣时,为了方便提高工效,官兵们脱下了军装,只穿个大裤衩。在一次打风枪钻炮眼时,我和几个战友正在聚精会神操作,突然,面前出现塌方,巨石向我们砸来,排架和人员全被淹没。当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不幸中的万幸,危石不厚,只是受了点轻伤,当天晚上,我又上了工地,也因此获得了三等功。然而,我有21名战友却永远地留在了工地现场。经过一年零四个月,我们高标准完成了“引滦入津”工程。之后,铁道兵集体兵改工,我们又脱下军装,正式成为天津市民中的一员。
现在,随着“南水北调”至天津,天津人喝水问题早已解决,回顾我们因水而结识、居住生活的城市,看看海河的坎坷历程,突然萌发一种想法:“海河如父”。是的,海河,就像父亲,是那样的稳如泰山、处事不惊,在默默无闻中容纳了千年兴衰、不离不弃,把汩汩细泉汇入大海,成就了今天两岸的辉煌。

武新才,籍贯山西高平,十八岁参军至津,武清区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歌、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新闻专著5部,作品约300万字,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级相关奖。
◉美文
陆慧敏 | 教室很小,世界很大
真想一觉醒来,我在小学的教室,对同桌说,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啊!
【一】
柳絮隔着窗户飘了进来。记忆中见过最壮观的一次飘絮,就是在小学的操场上。漫天飞舞的絮,如雪片一般,覆盖了整个天空。一阵风过,起起伏伏。我们被携裹其中,兴奋地到处抓这抓那。
那时对这些毛茸茸的东西,根本无“过敏”一说。因为知识浅陋,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只是用土法敷衍解决。我家婶子,就是个典型的过敏体质。春天上山采茶,不出半个时辰,浑身上下就会生出大大小小的板疙瘩,钻心地痒。周围人都说,那是“怕青”,多在山上待待就好了。结果,就这样几十年的“锻炼”下来,现在也好了。
我读三年级时,一次在家做作业,把圆珠笔帽吸进了喉咙,顿时吓得大叫。我妈不问缘由,直接把我拽进厨房,伸手就从盐罐里,捉了一大把盐,让我张开嘴直接吞。连续吞了三四把盐,她才问我怎么了?我说是圆珠笔帽子卡进喉咙里了,她说,我以为你是喉咙突然起泡堵住了,所以吞盐齁破。
结果圆珠笔帽子还卡在喉咙里,出吸气都能带点响声,我伸手似乎从喉咙处都能摸到。但我妈说,吃了盐就没事了,能消化掉!现在回想,真觉得这种土法非常不可思议。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有次打喷嚏,一下子又把圆珠笔帽子从嘴巴里吐出来了。
农村生活,有时就是这么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也正是乐趣所在。
采茶是件看着很美的事情,但茶树丛中到处都是野蜂巢,一不小心手就伸进去了。春天在长满红花草的田里玩,跑着跑着,就会看见不远处的草在晃动,顷刻间,就会左右分出一条明显的曲线。胆子大的,几步冲上去,就会捉住蛇的尾巴,然后提起来一个劲地抖,到处摔着去吓人;胆子小的,马上尖叫一声,跑得比蛇都还快。
我就曾在河边的菜地里,见过小伙伴们捉住这样一条乌梢蛇。它匍匐在草丛处,感到人走路的震动后,就沿着长满青草的菜地往水田里跑。从青草倒伏的状况看,肯定是一条大蛇。胆大的同学一个箭步冲上去,用穿着拖鞋的脚,一下就踩住了蛇的头。我前去帮忙捉它,蛇的尾巴沿着我的胳膊,一直往上缠,越来越紧。那种冰冰凉的感觉,直到现在回忆起来,还感觉头皮发麻。
蛇被捉住后,用新剥的柳树皮拴住了脖子,挑在竹竿上。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带进了学校,上课的时候,就把蛇挂在围墙外的那棵老沙柳树上。一下课就跑过去看看,一会摸摸它,一会捏捏它。
再后来,这条蛇被学校的一个老师看上了。说这么好的蛇,都快被你们玩死了,不如吃了吧。
于是放学的时候,用老师拿来的剃须刀片手忙脚乱地开始给蛇剥皮。老师则端着一杯水,站在旁边看。剥到一半,从胸部取出一物,递给老师,说,是蛇胆,可以明目。老师喝了一口水,直接丢进嘴里,吞了。快剥结束的时候,又从蛇腹部取出一物,一同学说,这才是蛇胆,刚才那是蛇心。老师面无表情,依旧是喝了一口水,又把那一物丢进嘴里,吞了。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记忆最深的有两次。还有一次是在我家对面的小河,是一条菜花蛇。捉住后,也是难逃一死。几个熊孩子把蛇皮装满水,呈X状背在背上,到学校招摇过市,到处吓女同学。蛇肉当时就扔在蓄满水的稻田里,我用手去摸时,它还在动,似乎想缠住我的手。我才不怕了,让它缠,反正就那一截。
【二】
春天的稻田里,到处都是一簇簇黑乎乎的小蝌蚪,旁边的小河里也是一簇簇的。还有从小河引水灌溉时,经常能捉到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的鲫鱼。掬一捧水,就捉起来了。
春天的小鱼真是特别的多,河沟里,稻田里,水库里,山塘里,但凡有水的地方,都是他们的乐居。尤其是到了夏天,几场大雨一落,水漫山塘,鱼就顺流而下。
我见过最震撼的一次,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小水库因暴雨翻埂,鱼就顺着小河成群结队地狂奔突进。整个生产队的人,家家都拿着装衣服的竹篮在河边守株待兔,一竹蓝下去,总会撞上一两条两斤左右的大鱼。
后来因为雨越下越大,河水暴涨,再也无人敢靠近。成群结队的鱼,如万马狂奔,拥挤着往下游跳,颇有抢着跃龙门的感觉。那一刻,你只有亲眼见证了,才会发自内心地承认,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神迹存在的。
鱼捉回来后,多半都是清炖,红烧的很少。我也不知道为啥。估计是做起来太费事,家里农活又忙,没那个闲工夫慢慢烧。
我妈就常念叨,“烧鱼没有巧,就是要煮好”,还有就是,“鱼煮三滚,吃的安稳”。那时,我们吃的比较多的,都是小河鱼。夏天在河里洗凉水澡,鱼多的都撞腿。河水浅的时候,鱼喜欢躲在石头下面,捉时,要么拿个大铁锤,直接往石头上震。只要力道得到,一锤下去,肯定有鱼昂着头往外面跳。还有就是用手直接摸,有时需弓着身子,耳朵都贴着水面了,双手呈包围状,伸进水底的大石头下,沿着石缝一点点往中间摸。
有次在我大姑家的小河里摸鱼,手伸进去时,感觉肉呼呼的,心里一喜,赶紧就把双手往中间慢慢拢。快合并的时候,突然看见有条小水蛇浮头伸出水面,吓地立马把手缩了回来,那小水蛇还一动不动,盯着我看了许久,才悠悠地游走。
除了摸鱼,捉河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闷鱼。
方法也很简单,选个竹筛,内置一石块,表面蒙上纱布或塑料薄膜,在中间掏一拳头大小的洞,里面撒上米粒或用香油拌的麦麸。把竹筛沉入水中,小鱼会顺着麦麸和米粒的香味游进去。用这种方法,我只花了小半天时间,就曾捉到过十几串河鱼。捉到后,就用狗尾巴草,从鱼鳃处穿过,一串十几条,提着回家。
家里大人心情好的时候,就炒个辣椒什么的。忙的比较烦躁,就会甩下一句,“要吃自己搞”。这种情况,鱼多半是要么喂了鸡,要么喂了鸭。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家的鸡鸭多半都是散放的,包括猪也是的。只是到了后来,家里建了猪圈之后,才把猪关起来。但鸡鸭鹅还是散放。散放最大的问题就是毁庄稼,不仅是自己家的,还有别人家的。
家里菜园地刚种的小青菜,一个下午就可能被啄得只剩光杆。路边的稻田也是一样,凡挨着路的稻穗,基本颗粒无收。每次只要家里的菜地被啄,无论和我有无责任,父母说着说着,就讲到我头上来了。什么不能放学回来早点啦!你看哪家的某某某,他好“巴家”,知道一放学就往家跑。什么,做事一点不尖心啦,只晓得玩,家都快被人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啦。等等!
那时经常大半夜的,我和妈在稻田里到处找鸭子。因为日落后,鸡只要吃饱了,就很自觉的就进笼了。而鸭子,往往跑到半人多深的稻田里,找不到出来的方向。大半夜的,还在田里嘎嘎叫。我妈又怕鸭子被野物叼了去,两个就挽着裤脚下田去找啊。
我打着手电筒,我妈举着竹竿。听见鸭子在哪里叫了,手电筒一束光照过去,她便赶着稻禾,像波浪一般,一遍遍地往田埂上撵。最让人恼的是,赶了半天,眼瞅着快出田了,鸭子不叫了。顿时失去了方向。过了十几分钟,又听见鸭子在田中间叫着欢。
每次捉到之后,她都狠狠地骂,“这个畜生,明天就把它杀掉炖汤”。结果一直都舍不得杀,慢慢地熬到过年。等到有南方人背着蛇皮口袋,挨家挨户地叫着收鸭绒的时候,它的“大限”就到了。
后来,我家还养过“洋鸭子”,就是那种会飞的“鸷”。养了三只。有天没关住,扑啦啦就飞到对面的山上去了。当天晚上,家里就把剩下的两只杀掉了。
那时每年夏天,我妈不知从哪听来“偏方”,说夏天吃三鲜汤大补。所谓的“三鲜”,就是鸡、鸭子、猪肉,在一起炖汤。为了防止我和妹妹偷吃,她会把炖好的汤,放在碗橱的最高层。被我知道后,就端个椅子,和妹妹站在上面,一会偷吃一块,一会又吧唧嘴,问妹妹,好吃吗?她说:好吃。我说:那我们再吃一块吧。
偷吃后,为防止被发现,就把骨头扔在碗橱底下。到处游荡的猪,闻到香味后,直奔厨房,一下就用猪鼻子把碗橱顶翻了。我和妹妹都没敢道出其中缘由,就说是猪把碗橱顶翻了。
那天晚上,猪没有再喂食,在圈里嚎到半夜。
【三】
农村养猪,吃的都比较糙。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心细的人家,还经常打猪草,回来后,用大锅煮熟,放上糠,一起煮煮。
我们家的猪,几乎就没吃过熟食。我一放学回家,就拿着竹篮去田里或大塘里捞浮萍,回来后,用大锹一顿乱扎,再用一瓶热水,烫半桶糠,两者一起拌拌。有时猪不吃,我妈就会跑到猪圈门口,指着猪槽,像训斥小孩一样:“这个吃不得你啊,给我赶紧吃。”
所以每年过年杀年猪的时候,我家杀的猪,都不会太大,基本在100斤左右晃荡,而且精肉都比较多。有次,生产队的一个同学问我,你家的猪,怎么肠子那么细,我家的太肥了。我直接告诉他:饿的!你家猪像我家这样,经常饿饿,不仅肠子细,而且精肉多。
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童年和少年是非常快乐的。我4岁上学,那时村小学刚开始招收第一届幼儿班,天天在家背个书包吵着去学校。我爸好像攫住了一束“家族之光”,以为是块读书的材料,兴冲冲地跑去给我报了名。不过从后来的学习成绩看,实在是伤了这位老人的心,一共读了两个幼儿班和两个一年级。
也正是因为比别人“多读了两年书”,可能我的童年也就相对的比别人长了些时日。散学时,故意远远地走在队伍后面,去路边的修车铺,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里寻一粒钢珠,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枫树做的陀螺,用小小的手,捏着小小的刀片,在底部挖上一个小洞,把钢珠楔进去,再找块石头磨平底角的毛刺。抽出劳保鞋上的黄色鞋带,一口气跑到粮站的水泥广场上,我能在那抽打上一两个小时。抑或去大平地的老屋晒场,在那和几个同学划上一个大圆圈,掏出弹珠,撅着屁股,杀得难分难解。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还会上山去撅一把兰草花,或者一大束映山红。把鲜嫩的映山红放在嘴里大嚼,满嘴血红。还会去茶地和河沟边翻找鸟窝,每次都是轻轻地把那两枚蓝色的小蛋拿出来,放在手掌细细端详。
后来又学会了用茅草做音管,吃掉中心嫩嫩的芯,中空的部分能吹出各种不同的音调;剥柳树皮作卷筒哨子,吹出来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用小竹管子作吹筒,在嘴里塞上一把野豌豆,一鼓气发射出去,突突突的像机关枪一样。
用一个破瓷缸舀满水,在弯曲遒劲的树根处掏出一个洞,找来松针和枯树枝,塞进在下面把水烧开,往里面放各种野果,煮出一缸不知什么味道的汤。还把废弃的红砖头,很有耐心地慢慢敲出小块,研磨出细细的粉,学着医生的模样,用一张张废纸包好,当做“能治百病的药”,分发给一个个小伙伴。
每天上学时,斜跨的破黄帆包拍打着屁股。生产队里,哪家有事都喜欢跑去凑凑热闹。有人结婚,我跟着跑去闹洞房,看看新娘长得是否漂亮;有人建房上梁,我就跑去抢喜糖;有人生孩子,我总想挤进人堆去,看看婴儿吃奶和啼哭的模样;还有老人去世的,挺在屋中的棺材板上,我总会偷偷的摸摸他的手,看看是否像大人们所说的那般僵硬冰凉。
还有半夜里要热闹时,需有人围着棺材敲锣打鼓。我听几遍就悟出了鼓点,然后背着小牛皮鼓就围着棺材敲上,1、2、3、4,5、6、7……1、2、3、4,5、6、7。除了敲鼓之外,还要用黄表纸叠“元宝”,用麻秸秆和竹签做成的小屋子,外面糊上各种颜色的纸。里面会放金童玉女、家具用什一应俱全。
虽然说,农村风水观念很重,觉得这些东西晦气,但我就喜欢看,而且真真觉得这是一件绝好的艺术品。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四】
我那时还整天沉迷去做一个大侠。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弓箭,用竹片和细钢丝拉起的弓,用伞骨一头磨尖做成了箭。每次出场,必把破被单往脖子上一系,一席披风拖地,把弓箭往肩上一搭,心中满是寒山孤影,江湖故人,看见什么都是弯弓一箭。
门前的柳树,栅栏上的葫芦,草丛里的冬瓜,甚至树梢上的马蜂窝,都是目标。后来,还用杉树削成了一把宝剑,跑到菜地里,奔到田野里,对准拔节的野菜,开花的小鹅草,伸出触角爬树的藤蔓,各种快意恩仇,手起刀落。那就是我心目中理解的整个江湖。
我每天都沉迷在大自然的五光十色之中,流连于各种好玩的游戏之间,以致往往在酣梦之中,都还沉浸于此,兴奋地突然大叫。我的妈妈一度以为我是撞某种邪物,到处托人,准备去给我“算算”。
后来我长大了些,人既大了,玩的东西自然也多了。再也看不上逮雀捉蟹、跳马射箭这些“小儿科”了。夏天的时候,会偷偷背着大人和一帮同学去大河里“洗冷水澡”,满河都是赤光光的身体。会游泳的慢慢划到河中间,各种狗爬,哼哧哼哧来,又哼哧哼哧去。不会游泳的,就在浅处,像乌龟一样趴在水面上,一脚踩着河底,一脚使劲地扑腾着水,努力做出一个资深泳者的样子。
我妈照例总为我担忧,惟恐一不小心就会被水淹死。她会编各种怪力乱神的故事,以期达到阻止我的目的。她能把类似《聊斋》里冤鬼托生的段子改个时间和地点,一脸正经地跟你说,多年前河里曾淹死过一个老太太,冤魂不散,就等着有人下水,然后捉住他的脚拽入水底,让他溺死在这,如此,伊方能转世超生。
这个故事有段时间对我很起作用,当再去“洗冷水澡”的时候,每每遇到河底冰凉的暗流淌过脚背,总感觉像有人捉住了我的腿,心里一阵惊慌,条件反射似地快速蹦上了岸。后来遇到次数多了,慢慢地也就麻木了。
每天中午照例跑到河里“洗冷水澡”,我妈一觉醒来,在凉床上看不到我,就会执着一跟竹篾条到河边走一趟。因为在时刻警惕着,当她还没走近,我早早地就爬上了岸,抱着一堆衣服,躲到桥墩后面。清楚地听她在向其他人问来问去,然后一面悻悻然地离开,一面恐吓泡在河里的那些伙伴,回家如何告状他们的父母。
既然没让她擒住,回家后肯定要把自己收拾得不露一点痕迹。把头发和内裤晒干是必须的。也有大意的时候,内裤没干就急急地穿,结果外罩的长裤很明显被湿印出了内裤的形状。什么也不必说,看到眼神不对,就要赶紧跑。
她一面拿着竹篾条在我后面追,一面撂下狠话,“你是野人差不多,晚上回来试试”。
再后来的时候,我又迷上了斗“跑得快”“五十K”和叠纸牌。为了凑齐一副完整的扑克,从各处寻来各种花花绿绿的牌面。小小的手,根本握不住13张牌,每次都把顺子、三带俩,一个个的码齐扣在地上,最终能捉在手里的,往往只剩下了两三张。
自从精于这项“脑力运动”之后,一到放暑假,整天就把纸牌用橡皮筋勒成一叠,揣在裤兜里,看见般大的伙伴就凑上去,把那叠牌从兜里掏出来:“可斗牌?到我家打。”
纸牌打的时间久了,自信心开始极度爆棚。总感觉自己一身本事无处彰显,必须要证明一下。刚开始还无甚赌资,后来开始撕读过的课本,那一张张纸当做一张张钱,从《语文》书一直撕到《自然》书,最后的一点本钱,连暑假作业都被输的精光。
我大舅家的老表,牌技了得,每年暑假到我家来,走的时候都是满满一书包的纸。到他家去上茅房,满粪缸里扔的都是我的一页页课本。
后来扑克牌确实没打了,但我又迷上了打弹珠。
伏在地上,用一只眼睛瞄准,然后用大拇指使劲地弹出去。时间一久,整个大拇指的指甲盖都被磨成薄薄的一片,晚上洗脸的时候,热水一泡,钻心的疼。这依然没能阻止我好玩的本性。
弹珠多的时候,为了不被大人发现,就像小松鼠冬天储存食物一样,在家里到处藏:墙缝里,枕芯里,树洞里,在屋檐下挖坑埋上,甚至还爬到我家对面山上,藏在一个险要的山峰处。
无一例外,这些弹珠后来找到寥寥,多半是自己都不记得到底藏哪了。前年家里翻修新房,挖掘机把墙面推倒之后,我还在废墟之中发现了一捧弹珠,依然光洁如新,用作业本包裹着。
再后来,我离开了农村,前往外地求学,去感受另一个世界,接受另一种人生教育。现在偶尔回家,还是喜欢去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就是为了记忆中的那一派空气,一阵声音,一分颜色,虽然乡村现在变化极大,早已物是人非,但就是在那站一站,就够使我觉得满意。
真想一觉醒来,我在小学的教室,对同桌说,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啊!

陆慧敏,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新闻从业工作16年,长期从事社会调查新闻和安徽地域文化报道。作品先后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安徽新闻奖。
轮值主编|王冠
